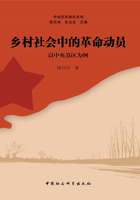
绪论
著名哲学家、乡村建设实践家梁漱溟曾认为:“中国农民散漫非常,只有个人,不成阶级。将如何期望他们革命?将如何依以为基础呢?在革命家想象他是绝对革命,其实他是与革命无缘的!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除非他们失业流落,或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者然即至于此,仍未见得 ‘绝对革命’。” 然而事实上,正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成了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那么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呢?要解释这一问题,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活动及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显然颇有必要。
然而事实上,正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成了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那么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呢?要解释这一问题,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活动及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显然颇有必要。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为主体的中央苏区范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行社会动员,使革命的影响和观念深入乡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实现了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与革命的统一,建立起一个从上而下一体化的动员机制,使农民真正进入了革命的行列。可以说,中央苏区革命政权的发展壮大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是离不开的,广泛的社会动员是乡村革命的重要环节。革命在乡村社会的深入需借助一系列的动员活动才得以实现,动员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其实际效果直接关系到各项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考察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活动,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可以从苏区政权与乡村社会上下互动的视角来审视中央苏区历史的发展过程,以此深化对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认识。以往学术界的乡村革命研究,读者所看到的多是革命话语系统中的少数领导者和革命政权的活动,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和行为变动则隐而不明;在分析苏区历史事件时,多聚焦于党政的中央层面活动,而对于苏区兴衰的原因多以路线政策正确与否来进行解释。革命政权建设是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它的革命氛围不是打倒了地主政权、分田地、取消地租和高利贷就自然形成的。只有苏区的各项政策与乡村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察,方能比较清楚地认识中国乡村革命的真实路径和实际场景。
苏区有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区别说明了革命动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群众基础较好的老苏区其实是共产党人用尽心力才建立起来的。农民不会因为获得好处就自然支持苏维埃政权,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一般来说是静态的保守力量,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中央苏区原来是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一度大量存在的仇视苏区政府的“土围子”基本上是这种宗族力量的集合。例如,中央苏区兴国、于都、宁都和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的群众“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 ‘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里” 。那么,在国民党政权的强势包围之中和传统社会生态下,革命政权如何能扎根、繁茂?这期间经历的过程显然有待更深入、微观的研究。正如研究者指出:“在研究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对农村革命的作用时,不能泛泛地谈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局势,不妨对党在实施动员时逐步摸索出的一些具体技术细加考究。可以研究这些技术的创造、示范、推广、演变,研究上级、具体执行者和群众之间在这些技术方面彼此作用的过程。”
。那么,在国民党政权的强势包围之中和传统社会生态下,革命政权如何能扎根、繁茂?这期间经历的过程显然有待更深入、微观的研究。正如研究者指出:“在研究共产党的组织动员对农村革命的作用时,不能泛泛地谈意识形态和国内外局势,不妨对党在实施动员时逐步摸索出的一些具体技术细加考究。可以研究这些技术的创造、示范、推广、演变,研究上级、具体执行者和群众之间在这些技术方面彼此作用的过程。” 因此,了解苏区的革命进程应从各项革命政策在乡村中的深入过程、乡村社会对革命接受和参与程度,去进行微观的考量,而各种革命动员活动的进行无疑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
因此,了解苏区的革命进程应从各项革命政策在乡村中的深入过程、乡村社会对革命接受和参与程度,去进行微观的考量,而各种革命动员活动的进行无疑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
其次,有助于通过政治与社会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对中央苏区的各项政策进行动态的考察。革命动员是革命政权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的具体体现,因此,应具体了解其过程和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具体的革命动员活动中的社会性因素和社会变化进行研究,弥补了单纯从中央政府的文件、政策和制度层面去研究苏区史而忽略苏区各项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的不足。对于苏区一些政策未达到预期目的,不能仅以笼统的“左倾”错误一语作为解释,而是应结合具体的历史场景做细致的考察,进一步探究其中深层的社会性、结构性的因素。
中央苏区革命动员活动体现了政治活动中人的活动对政策实施效果的重大影响。例如在苏区推行公债过程中,中央政府鼓励群众自动购买,并对具体的工作方法作了要求:“反对平均摊派,就是要鼓励群众自愿地买公债。买得多的要把他的名字并所买公债的数目在乡苏门前,出榜示众,以作模范。不肯买的绝对不能强迫他买,要由乡苏代表、妇女代表会的代表及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去劝他买,去鼓励他买,可以要那些买了公债的去劝其他没有买公债的。可以把买得多的人,每村组织一个宣传队去进行推销公债的宣传。” 但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却采取中央极力批评与反对的方式来进行。如石城珠江区乡苏推销公债票时:“只是把公债票照他自己的意思摊派一下,送到各个群众家里,不管他有钱无钱,一定要销他所摊派的数目。群众不肯接受,他就在他们的桌子上一放,说 ‘随你要不要,我就要写你的数’。有的群众真拿不出钱,要缴款时,有将饭锅送到代表家里抵数,也有把棉被当掉来偿公债票的。”
但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却采取中央极力批评与反对的方式来进行。如石城珠江区乡苏推销公债票时:“只是把公债票照他自己的意思摊派一下,送到各个群众家里,不管他有钱无钱,一定要销他所摊派的数目。群众不肯接受,他就在他们的桌子上一放,说 ‘随你要不要,我就要写你的数’。有的群众真拿不出钱,要缴款时,有将饭锅送到代表家里抵数,也有把棉被当掉来偿公债票的。” 这种情况表明,革命动员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偏离,而这种偏离对政策的效果和乡村社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具体的革命动员来考察基层政府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乡村革命的认识,避免在研究中局限于文件和制度而得出过于宽泛的结论。
这种情况表明,革命动员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偏离,而这种偏离对政策的效果和乡村社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具体的革命动员来考察基层政府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乡村革命的认识,避免在研究中局限于文件和制度而得出过于宽泛的结论。
动员是一个与革命及战争相关的术语,是指被战时热情所激发,寻求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有计划的大规模运动,旨在发动群众支援战争。亨廷顿是较早从政治学角度解释了“动员”的含义,他将发展中国家中的政治参与分为动员参与和自动参与两种类型,并分析了穷人的动员参与的特点。![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小寿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133—14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C845F/10797208104918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35.png?sign=1738833609-fUJ5ocOpEIuod24jeDxAFq5U1AkJmibB-0-00f64ee7d60d2a4e68e88d86d9b9cde4) 而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动员应分为社会动员和革命动员两种;相比于社会动员,革命动员是对政治体系的交流功能的控制,而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革命,就是通过革命动员来控制交流网的。
而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动员应分为社会动员和革命动员两种;相比于社会动员,革命动员是对政治体系的交流功能的控制,而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革命,就是通过革命动员来控制交流网的。![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C845F/10797208104918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35.png?sign=1738833609-fUJ5ocOpEIuod24jeDxAFq5U1AkJmibB-0-00f64ee7d60d2a4e68e88d86d9b9cde4) 就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革命叙事方面的题材一直是比较关注的,对苏区史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随着以往宏观的革命叙事向当前微观的叙事方式转变,学者们更加重视革命时期的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此相关,学术界对苏区的革命动员问题亦进行了研究,相关成果可以大致归纳如下方面。
就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革命叙事方面的题材一直是比较关注的,对苏区史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随着以往宏观的革命叙事向当前微观的叙事方式转变,学者们更加重视革命时期的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此相关,学术界对苏区的革命动员问题亦进行了研究,相关成果可以大致归纳如下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动员政策的研究。中共革命的传统解释认为,针对农民在土地分配不均和家庭贫困的压迫下这一状况实行相应的社会经济改革,直接促动了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这种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内的中共革命史全史研究中,如胡绳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 除土地分配因素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也是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如美国学者汤森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他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
除土地分配因素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也是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如美国学者汤森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他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参见[美]汤森《中共政治》,顾速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C845F/10797208104918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35.png?sign=1738833609-fUJ5ocOpEIuod24jeDxAFq5U1AkJmibB-0-00f64ee7d60d2a4e68e88d86d9b9cde4) 美国学者塞尔登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于发动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农民阶级是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发生革命转变的。相比而言,赋税改革比减租减息更为重要,赋税改革成为连接中共和农民的纽带。
美国学者塞尔登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于发动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农民阶级是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发生革命转变的。相比而言,赋税改革比减租减息更为重要,赋税改革成为连接中共和农民的纽带。![参见[美]马克·塞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C845F/10797208104918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35.png?sign=1738833609-fUJ5ocOpEIuod24jeDxAFq5U1AkJmibB-0-00f64ee7d60d2a4e68e88d86d9b9cde4)
二是关于革命组织的研究。学者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无论是土地分配不均苛捐杂税繁重,还是土地改革和减轻赋税等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族主义情感的上升,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都与革命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和接纳共产主义诉求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互关系。相反,革命在一些地方的极大成功,只是由于共产党碰巧在那些地方建立了组织,或者也可以说,革命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的确定不移的事实。 美籍华裔政治学者邹谠进一步指出:中共革命并不是自发的,它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灵活的战略策略。除非行动者认识到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对他的选择具有结构性的约束,并使自己的选择与这种约束相适应,否则他将不可能取得胜利。
美籍华裔政治学者邹谠进一步指出:中共革命并不是自发的,它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灵活的战略策略。除非行动者认识到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对他的选择具有结构性的约束,并使自己的选择与这种约束相适应,否则他将不可能取得胜利。![参见[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4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C845F/10797208104918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35.png?sign=1738833609-fUJ5ocOpEIuod24jeDxAFq5U1AkJmibB-0-00f64ee7d60d2a4e68e88d86d9b9cde4)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经济基础有助于革命的发生,但中国共产党进行主动选择和行动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台湾学者陈永发通过对中共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认为,发动农民并非民族主义那样自然而然和简单,中国共产党推行的社会经济纲领再分配政策符合农民的利益,对发动农民抗战发挥了作用。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运动主要取决于对农民的操纵和对地主的镇压。他从斗争以及对斗争操纵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的成败。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经济基础有助于革命的发生,但中国共产党进行主动选择和行动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台湾学者陈永发通过对中共华中华东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认为,发动农民并非民族主义那样自然而然和简单,中国共产党推行的社会经济纲领再分配政策符合农民的利益,对发动农民抗战发挥了作用。不过就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运动主要取决于对农民的操纵和对地主的镇压。他从斗争以及对斗争操纵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的成败。 何友良指出,农民的奋起革命的发生,除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之外尚须另一个必备的条件,即有先进的个人和组织新的思想理论来揭露社会的腐败、人民的困苦和规划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热情投身于社会变革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广泛深入动员的结果。动员给他们输入了新思想,使他们产生了新认识,进而影响或改变了他们的眼光与行为。正是通过先进政党的教育灌输,苏区农民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广泛接受新知识,普遍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思想倾向明确,敢爱敢恨,爱憎分明,阶级观念增强。
何友良指出,农民的奋起革命的发生,除了贫困的社会根源之外尚须另一个必备的条件,即有先进的个人和组织新的思想理论来揭露社会的腐败、人民的困苦和规划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热情投身于社会变革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广泛深入动员的结果。动员给他们输入了新思想,使他们产生了新认识,进而影响或改变了他们的眼光与行为。正是通过先进政党的教育灌输,苏区农民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广泛接受新知识,普遍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思想倾向明确,敢爱敢恨,爱憎分明,阶级观念增强。 陈德军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例指出,处身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与处身于革命之中的农民之间需要一些过渡的途径才能连接起来,革命本身不会不胫而走。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其以经济生活水平来解释革命在某一地方的发生发展,倒不如从社会的分裂散沙化的程度来寻找理解革命及其表现形态的线索更为合适。
陈德军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例指出,处身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与处身于革命之中的农民之间需要一些过渡的途径才能连接起来,革命本身不会不胫而走。从某种角度来说,与其以经济生活水平来解释革命在某一地方的发生发展,倒不如从社会的分裂散沙化的程度来寻找理解革命及其表现形态的线索更为合适。
三是对动员对象行为的研究。研究者从自上而下的视野分析农民为什么能被动员起来的问题时,往往缺乏农民自身的声音,尤其是缺乏对农民个体或群体感受的关怀。对此,不少学者主张,讨论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革命理应首先对农民主体的心态和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否则,无法解释在同一外部条件比如经济政策社会动员、外国侵略,或同一社会经济基础比如土地分配不均生活贫困之下,为什么有的农民参加了革命,有的农民却没有。因此,革命只有与个体的需求重合,才会吸引他们参加革命组织和参与革命活动。裴宜理指出,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或不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强调情感作用在革命动员中的观点并不排斥其他可供选择的对于革命胜利的解释。但是,如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的话,它或许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诸如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符号体系,甚至阶级划分等受到情感影响的多种方式。![参见[美]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C845F/10797208104918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35.png?sign=1738833609-fUJ5ocOpEIuod24jeDxAFq5U1AkJmibB-0-00f64ee7d60d2a4e68e88d86d9b9cde4) 周锡瑞认为,陕甘宁边区农民参军的动机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显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但很多人说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是因为家庭或个人方面的原因。总之,考察一下最初参加革命的那些农民的生活经历和动机,就会发现许多人参加红军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谈不上民族主义,这些民众同动员和政治参与也不沾边,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
周锡瑞认为,陕甘宁边区农民参军的动机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显然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但很多人说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是因为家庭或个人方面的原因。总之,考察一下最初参加革命的那些农民的生活经历和动机,就会发现许多人参加红军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更谈不上民族主义,这些民众同动员和政治参与也不沾边,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参见[美]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42—545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C845F/10797208104918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35.png?sign=1738833609-fUJ5ocOpEIuod24jeDxAFq5U1AkJmibB-0-00f64ee7d60d2a4e68e88d86d9b9cde4) 黄琨认为,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一部分农民参加了革命。革命农民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只有当革命的口号与农民的个体生存感受产生共振,并且革命的组织能够提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安全感时,才能吸引他们加入。
黄琨认为,贫困并不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唯一理由,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一部分农民参加了革命。革命农民固然出于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但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义准则仍在考虑之列,革命所面临的风险也常使他们迈不出革命的脚步。只有当革命的口号与农民的个体生存感受产生共振,并且革命的组织能够提供给农民所需要的安全感时,才能吸引他们加入。 黄道炫认为,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走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
黄道炫认为,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走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
四是关于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同那种只强调革命动员对乡村社会影响的单线式思维方式不同,这种研究也关注了乡村社会对革命动员的反作用,即从乡村社会的传统和广大民众的日常行为逻辑上去分析革命动员的过程和产生的效果,从而能较全面反映出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裴宜理从社会生态的角度以淮北地区为个案进行研究,试图解释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叛乱和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农民参加革命是基于生态上的、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特定策略。然而,这种为应付环境而确立的机制也可能削弱了人们最初对革命方式的接受能力。![参见[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4—265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C845F/10797208104918006/epubprivate/OEBPS/Images/35.png?sign=1738833609-fUJ5ocOpEIuod24jeDxAFq5U1AkJmibB-0-00f64ee7d60d2a4e68e88d86d9b9cde4) 万振凡分析了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传统结构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中共革命前江西乡村社会结构无论是结构要素、结构系统,还是整体结构都是一个典型的“弹性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减了1927—1937年江西乡村革命和改良中的绩效。
万振凡分析了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传统结构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中共革命前江西乡村社会结构无论是结构要素、结构系统,还是整体结构都是一个典型的“弹性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减了1927—1937年江西乡村革命和改良中的绩效。 王奇生指出,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为了恢复和壮大党员的力量,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给各省市委下达任务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组织。在此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在各地吸收党员,乱收滥拉。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或是出于个人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当地党的地方组织。
王奇生指出,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为了恢复和壮大党员的力量,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给各省市委下达任务指标,以期快速扩大党组织。在此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在各地吸收党员,乱收滥拉。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或是出于个人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当地党的地方组织。 钟日兴通过对中央苏区农民的“抵制”心态的分析展现了革命动员与农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中存在的动员方式不当和动员强度过大等情况影响了农民的生存伦理,在趋利避害心理的本能反应下出现了“赤白对立”“逃跑”“反水”等抵制现象,因此,农民的生存伦理安全是革命动员的基线。
钟日兴通过对中央苏区农民的“抵制”心态的分析展现了革命动员与农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中存在的动员方式不当和动员强度过大等情况影响了农民的生存伦理,在趋利避害心理的本能反应下出现了“赤白对立”“逃跑”“反水”等抵制现象,因此,农民的生存伦理安全是革命动员的基线。 曾耀荣则以1928年的永定暴动为例对近代城乡关系变动背景下的农民行为与中共革命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以来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联系性加强,另一方面它们的对抗性矛盾加剧,永定暴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永定暴动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推动农村革命的生动例证,也揭示出中共内部和农民在关于革命选择的不一致性及中共农村革命的复杂性。
曾耀荣则以1928年的永定暴动为例对近代城乡关系变动背景下的农民行为与中共革命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以来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联系性加强,另一方面它们的对抗性矛盾加剧,永定暴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永定暴动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推动农村革命的生动例证,也揭示出中共内部和农民在关于革命选择的不一致性及中共农村革命的复杂性。
以往学界对于苏区的革命动员已有一定的涉及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仍可进一步深化。如以往不少研究从“自上而下”的视角强调苏区政府动员政策、动员组织的重要性,或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农民的个体行为在革命动员中的选择,这些都不能全面体现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融合或是排斥、相互改变和相互适应的互动过程。这种情况决定了苏区革命的策略与具体实践之间经常存在着张力,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进行探究。
本书以苏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革命动员方法和措施,探讨革命如何深入乡村及其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以此深化对革命进程中的苏区政权与乡村关系的认识。在本书中分别通过早期暴动、政权建设、土地斗争、军事动员和妇女动员这些重大事件中所采取的具体动员措施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进行分别论述,突显苏区政府针对不同动员对象而采取的不同动员策略和产生的不同社会影响,以避免得出过于宽泛的情况;对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结合深层的社会性、结构性的因素对于动员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和效果进行分析;本书还力求客观地总结这一时期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中的经验教训,在论述苏区政权和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既反映革命深入开展和推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积极方面,也反映出革命动员中的一些不足。基于这些目的,本书的具体章节和主要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论述革命动员与乡村早期革命的关系。首先对乡村政权建设背景进行描述;其次通过分析早期革命动员的一些不足对乡村暴动的影响,来探讨革命动员与早期暴动的关系;最后对外来红军进入赣、闽乡村所进行的动员活动使革命形势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原因进行探讨。
第二章,通过革命动员措施的分析考察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的深入过程。首先考察苏区对乡村苏维埃机构的健全和演变过程,其次考察苏区政府保障了群众的民主权利的措施,最后考察建立群众团体组织的措施。
第三章,通过革命动员措施的分析考察土地斗争在乡村社会的深入过程。首先考察分田运动中采取的动员措施,其次考察分田运动中采取的动员措施,最后从正反两方面考察土地斗争中的革命动员产生的效果。
第四章,通过革命动员措施的分析考察军事动员在乡村社会的深入过程。首先考察扩大红军方面的动员措施,其次考察组织地方武装方面的动员措施,再次考察保障战时后勤供应方面的动员措施,最后从正反两方面考察军事斗争的革命动员产生的效果。
第五章,通过革命动员措施的分析考察妇女解放运动在乡村社会的深入过程。首先考察共产党人对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其次考察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动员措施,最后从正反两方面考察军事斗争的革命动员产生的效果。
第六章,考察苏区革命动员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首先,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成果,其次考察乡村社会的抵制现象及其与动员的关系。
结语部分,就革命动员对乡村革命进程的影响,革命动员中的中央政府、乡村政权和民众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总结,并分析对今天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