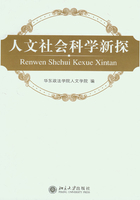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管理中的中外冲突
开埠后的上海城市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格局:一方面,随着租界的开辟、发展和繁荣,一个统一的城市被分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租界和华界;另一方面,在小刀会起义以后,租界社会内部也形成了华洋杂居的局面。因此,不管从城市总体上,还是在某些局部区域,都是中外聚集、华洋杂居。华界、租界尽管相对独立,但毕竟处在同一城市,有着利与害的共同点,会面临共同的问题,也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中外双方毕竟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在对城市的管理中经常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些共同的问题,手段、方式的不同经常成为中外双方争论的起因。而在租界内部,中外居民混杂,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风俗等,租界当局推行其城市管理措施时,也经常与中国居民发生冲突。本文拟以开埠初期上海城市社会中租界之交通管理、华界之城门管理、租界内之司法管理为例,论述开埠初期上海城市管理中的矛盾与冲突,以请教于方家。
交通安全:马车?小车?行人?
开埠后上海租界内之街道,很快就挤满了马车、小车和行人。据记载,在“居留地还不到10年,就出现了马车”,这是一位史密斯先生(Mr.J.C.Smith)的私人财产,是一辆“非常时尚的四轮马车”。 此后,马车数量不断增加,马车的用途也由原来洋商巨贾的私人用车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公共交通工具。到19世纪70年代,公共租界规模比较大的出租马车经营企业已包括龙飞马市场、押卜禄马房、虹口马房、二摆渡马房等。
此后,马车数量不断增加,马车的用途也由原来洋商巨贾的私人用车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公共交通工具。到19世纪70年代,公共租界规模比较大的出租马车经营企业已包括龙飞马市场、押卜禄马房、虹口马房、二摆渡马房等。 小车,又称江北车、牛头车、羊角车、二把手等。原本存在江北农村,大概在清咸丰、同治年间进入上海租界,据记载:“上海初辟租界时,仅有江北人所推独轮羊角车,即今所称为二把手车,亦曰小车者。”
小车,又称江北车、牛头车、羊角车、二把手等。原本存在江北农村,大概在清咸丰、同治年间进入上海租界,据记载:“上海初辟租界时,仅有江北人所推独轮羊角车,即今所称为二把手车,亦曰小车者。” 小车不仅可以从事货运,还可以从事客运,因价格低廉、便利,发展速度非常快,1870年,公共租界、法租界对小车征捐发照时,当年月均捐照数达近千辆;而1873年,更达到2000辆;1875年,仅在公共租界捐照的小车就有2500辆。
小车不仅可以从事货运,还可以从事客运,因价格低廉、便利,发展速度非常快,1870年,公共租界、法租界对小车征捐发照时,当年月均捐照数达近千辆;而1873年,更达到2000辆;1875年,仅在公共租界捐照的小车就有2500辆。 实际数字可能远远高出捐照数,时人估计,1871年,上海洋泾浜往来小车就有数千辆之多。
实际数字可能远远高出捐照数,时人估计,1871年,上海洋泾浜往来小车就有数千辆之多。 有人估计则更高,称1870年就有小车约3000辆,1871年底则近万辆。
有人估计则更高,称1870年就有小车约3000辆,1871年底则近万辆。 至于租界内之人口,以上海公共租界为例,1855年,只有20243人;1865年,达到92884人;1870年,为76713人,这仅为公共租界内之常住人口,尚不包括大量的流动人口。笔者认为,在研究租界内街道的人流时,所谓的流动人口包括:(1)长期居住在租界,但为租界当局统计时遗漏的人口;(2)居住在华界,但经常出入于租界的人口。他们出入租界,或是工作地点在租界,或是流连于租界之娱乐场所,因此租界街道,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日子,人流非常拥挤。
至于租界内之人口,以上海公共租界为例,1855年,只有20243人;1865年,达到92884人;1870年,为76713人,这仅为公共租界内之常住人口,尚不包括大量的流动人口。笔者认为,在研究租界内街道的人流时,所谓的流动人口包括:(1)长期居住在租界,但为租界当局统计时遗漏的人口;(2)居住在华界,但经常出入于租界的人口。他们出入租界,或是工作地点在租界,或是流连于租界之娱乐场所,因此租界街道,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日子,人流非常拥挤。
租界内之街道比华界县城之街道宽阔得多, 而且市政当局还在道路两旁修建了专供行人行走的“子路”,即人行道。
而且市政当局还在道路两旁修建了专供行人行走的“子路”,即人行道。 当局也对马车、小车、行人的交通行为进行了规范。如法国领事就下令:“租地界内往来行人,每日下昼四点钟后宜从马路两旁行走,不得任意由中道而行。”
当局也对马车、小车、行人的交通行为进行了规范。如法国领事就下令:“租地界内往来行人,每日下昼四点钟后宜从马路两旁行走,不得任意由中道而行。” 在法租界公董局制订并公布的《肃清街道整顿铺家章程》中,第2条、第3条针对马车行驶进行了规定:“凡路上马车相遇须各让一半车路”、“凡马车夜行须有灯照”
在法租界公董局制订并公布的《肃清街道整顿铺家章程》中,第2条、第3条针对马车行驶进行了规定:“凡路上马车相遇须各让一半车路”、“凡马车夜行须有灯照” 。公共租界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规范马车行驶,如“令挂铜铃于马车之上”,“在行人烟稠密之街,十字转弯之路,切勿扬鞭驱马”,夜间行驶必须挂灯等。187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告示则对马车之行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如马车行走时必须靠左边;如超车,则必须“从右边过去”;在日落一点钟之后至日出一点钟之前,必须点灯,否则罚款五元;行驶于十字路口时,必须慢行,谨防发生碰撞;巡捕必须注意马车不能超速行驶等。
。公共租界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规范马车行驶,如“令挂铜铃于马车之上”,“在行人烟稠密之街,十字转弯之路,切勿扬鞭驱马”,夜间行驶必须挂灯等。187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告示则对马车之行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如马车行走时必须靠左边;如超车,则必须“从右边过去”;在日落一点钟之后至日出一点钟之前,必须点灯,否则罚款五元;行驶于十字路口时,必须慢行,谨防发生碰撞;巡捕必须注意马车不能超速行驶等。 可是,租界内之道路上,仍然经常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出版于同治时期的《上海新报》就经常登载一些交通事故的消息。如某日,“大马路有打野鸡者未详姓名,被马车冲倒,其车轮上由头顶滚过,下由小腹滚过,登时殒命”
可是,租界内之道路上,仍然经常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出版于同治时期的《上海新报》就经常登载一些交通事故的消息。如某日,“大马路有打野鸡者未详姓名,被马车冲倒,其车轮上由头顶滚过,下由小腹滚过,登时殒命” 。
。
道路如此宽阔,又有各自的交通行为规范,可是交通事故却如此之多,谁应该为道路交通事故负责?是马车?小车?还是行人?一场中外之间的争论由此展开。
在外国人看来,正是由于中国行人、小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他们认为,马车之所以经常撞伤行人,是因为行人不懂交通规则,因为马路本来就是“行马车之地”,行人之路在马路“两旁石砌街石”,可是往来行人不走两旁,偏向“路中而行”。 因此被马车撞伤,咎在行人而不在马车。
因此被马车撞伤,咎在行人而不在马车。
针对一些中国人对马车经常撞伤行人的抱怨,一外国人作出了这样一段回应:
盖人有一定当行之路,马车有一定当行之路,两不搀越,两无所妨,甚至马车联络而行或有十数里之遥,人行两旁子路,万无一失,上海马路之阔大,原所以为行马车地也,两旁听人行走,曾见马车敢在子路行乎,华人不解往往在马路中行走,且三五成群,并肩而行,东瞻西望,全无避忌,马车驶来则又惊慌失措,一有不慎,即遭其害,徒归咎于马车,晚矣。
一个外国人进一步评论说,为何“凡马踏车撞皆系华人罹此祸患,曾见有外国人受伤者乎” ?因为外国人知道“马路者,明系马行之路也”。可是中国人并不知道,因行走于马路中间,才受到伤害。
?因为外国人知道“马路者,明系马行之路也”。可是中国人并不知道,因行走于马路中间,才受到伤害。
相反,在中国人眼中,“西商所乘马车快捷则有之,稳当则未必尽然也” 。如果将马车伤人事故全归咎于行人,则为何有的行人并未违反规则,行走于街道两旁,甚至是在人行道上“贴壁而行”,也会祸从天降,遭到马车的侵害?
。如果将马车伤人事故全归咎于行人,则为何有的行人并未违反规则,行走于街道两旁,甚至是在人行道上“贴壁而行”,也会祸从天降,遭到马车的侵害?
闻礼拜一日虹口礼拜堂左近有一中国妇人带两小孩,长者约十龄上下,在前行走,其妇挽幼者之手在后行走,俱在子路上贴壁而行,并不在危险地也。乃祸从天降,猝不及防。突来某洋商马车,驶近前行小孩之旁,马失前蹄,全身扑下,马首撞在子路之阶石上,而前行小孩亦被撞倒,讵料小孩之首竟为马首所压,其马受伤甚重,生死未卜,而被撞之小孩更不问可知也。
因此,“洋场实是畏途”。并不是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是马车本身不安全,所以才引发了如此多的交通事故。
开埠以后的上海,在由一个前近代城市向近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我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惯等方面带有相当明显的农村生活特征。在我们的生活中,经验告诉我们,行走于道路中央才是安全的,相反于路边行走反而会带来危险。因此,西方所谓的人、车各行其道,行人走路边人行道,与车互不影响等生活习惯对我们来说,相当的新鲜和相当的生疏。所以,在上海街头,经常可以见到有人在马路中央“缓步当车” 。其实,在开埠初期的上海,人们除了对走人行道不习惯外,还对西方人严禁租界居民乱倒垃圾、随地小便、燃放爆竹等亦备感麻烦和不理解。
。其实,在开埠初期的上海,人们除了对走人行道不习惯外,还对西方人严禁租界居民乱倒垃圾、随地小便、燃放爆竹等亦备感麻烦和不理解。
城门:开?关?
在开埠前,城市管理中的城门是关还是闭,并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可是在开埠后,随着租界的繁荣,连接县城与租界的通道:老北门和新北门的开、闭就成为当时地方当局颇为头痛的问题。
在我国传统社会,城市一般都有城墙,有城墙也就有城门。城门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是保持城内外的沟通,一是防范各种外来威胁。明代上海筑城时,辟有六个城门。清同治五年(1866年)增辟障川门(即新北门)。这些城门派有士兵专门把守,一般在傍晚关闭,清晨开放。在传统社会并不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上海开埠以后,一些居民居住在城内,而工作地点在租界;有的居住于租界,而在城内工作;另有一些城内居民则热衷于租界的各种娱乐生活。于是关闭城门就给一些人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
在中国官府看来,晚上关闭城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所谓“宵小”黑夜进城,扰乱城内社会治安。因此规定“民间有事进出,钟鸣六点为期”,即晚上六点钟关闭城门,如果“寅夜擅入,定即提案责比” 。可是有人因种种原因必须在城门关闭以后进出,于是贿赂守门士兵、违规进出的现象经常发生。有人因此被枷号示众,“前月三十日城中打野鸡为业之顾某者归迟,以为新北门较老北门迟一点钟时关闭。遂由新北门而进,及至城下,不料已闭,因此踌躇待立,俟有人出入或可乘机而进,少顷有人至,叫城内,有人问曰,谁何,其人辄道姓名,当给洋一元始准开放,顾某窃喜,意谓得进矣,城门甫开,顾即先行挤进,守城者问曰,付洋者尔耶?顾某不答,仍欲前行,而付洋者在外喊曰,给洋者我也,于是执顾某,复启门而放彼入,当将顾某送至五老峰会防局内,次日解往县署,旋即枷号新北门口示众。”
。可是有人因种种原因必须在城门关闭以后进出,于是贿赂守门士兵、违规进出的现象经常发生。有人因此被枷号示众,“前月三十日城中打野鸡为业之顾某者归迟,以为新北门较老北门迟一点钟时关闭。遂由新北门而进,及至城下,不料已闭,因此踌躇待立,俟有人出入或可乘机而进,少顷有人至,叫城内,有人问曰,谁何,其人辄道姓名,当给洋一元始准开放,顾某窃喜,意谓得进矣,城门甫开,顾即先行挤进,守城者问曰,付洋者尔耶?顾某不答,仍欲前行,而付洋者在外喊曰,给洋者我也,于是执顾某,复启门而放彼入,当将顾某送至五老峰会防局内,次日解往县署,旋即枷号新北门口示众。” 顾某居住在城内,可是在城外租界工作——“打野鸡”,或许是“下班”太迟,被关在城外,希图“浑水摸鱼”,结果受到“枷号”惩罚,而顾某刚刚期满,又有人贿赂守门法国士兵,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受到惩罚。
顾某居住在城内,可是在城外租界工作——“打野鸡”,或许是“下班”太迟,被关在城外,希图“浑水摸鱼”,结果受到“枷号”惩罚,而顾某刚刚期满,又有人贿赂守门法国士兵,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受到惩罚。
晚上关闭城门,不仅给民间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给华界官方与租界的交通也增加了麻烦。官府因此规定,如有紧急“公事”,可凭官方所发“照会”进出。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些没有照会者专门在城门内外等待持照者,随同进出,往往一人之后,跟随者数十人,如此则城门形同虚设:
向来各城门于晚间落锁之后,遇有照会即行开放。但有照会者固当放出放入,而无照会者亦拥挤门下,一见有照会者则喜出望外。城门一开或一拥而进或一拥而出,反令有照会者退居其后,斯时盘查奸宄,何处盘查。
有的持照者则专门从事晚上带人进出城门的生意。《上海新报》记载:“有赖姓者,自本月初一日至十四日持第二十三号及第二十七号并第四十二号印着三张,在新北门小东门出入至十四次之多,且每次率领多人” ,上海道台不得不下令将这三张照会宣布作废。
,上海道台不得不下令将这三张照会宣布作废。
城门是否应该关闭,在中国官方看来是一个没有必要讨论的问题。而对外国人来说,关门是不可思议,且没有任何意义的。一外国人从几个方面对城门的关闭进行了评论:第一,他比较中西理念上的差别,认为中西都有城、有门,可是中国人“尚塞”,西方人“尚通”。其次,夜间关闭城门对于防盗也没有任何意义,反而给“居住城中而在城外贸易之人、居住城外而在城中贸易之人”的进出带来不便。而盗贼进城盗窃,“抑知盗窃于夜,盗不必夜间进城也,防于夜而不防于昼,吾知盗于昼间入城而守城者不知,盗早窃笑其旁矣” 。第三,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以“精明强干”之兵守卫城门,“无论昼夜城门洞开,听人出入,遇有形迹可疑之人或逐之或执之,必有能辨之者。如是有城有门可,有城无门亦可,闭胡为耶”
。第三,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以“精明强干”之兵守卫城门,“无论昼夜城门洞开,听人出入,遇有形迹可疑之人或逐之或执之,必有能辨之者。如是有城有门可,有城无门亦可,闭胡为耶” 。
。
在中国社会,用围墙建筑起来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因此在夜间关闭城门,防止城外暴徒对城市,即皇权的侵犯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传统社会中,有的城外有“廓”,如上海县城东部及东南部沿黄浦江一带,但这些地方的繁荣大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与政治、皇权基本无关。在皇权看来,它处在城外,与其他“暴客”一样会侵犯皇权的权威。上海开埠以后,由于租界的出现及繁荣,不仅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中心,也在同一个城市中新成长出一个政治中心。对于民间社会而言,或是因经济原因,或是因向往租界社会丰富的娱乐生活,不得不于城门关闭后经常需要进出。而对于官方来说,也经常因为“要紧公事”同样需要进出。现实的需要与城墙理念发生了冲突,于是就出现了人们跟随有照会者进出、贿赂守兵进出、以照会带人进出等被官方视为违规、犯法的事情。
罪与罚:轻?重?
开埠后的上海,因种种原因,社会治安状况相当差,于是,华界、租界当局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城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如1860年初,公共租界董事会认为,将“租界内华人住所及时地加以编号”是维护上海公共租界平静和良好秩序的一种较好办法,决定“华人居民由工部局出资,在每一家住所门前钉上一块马口铁皮,马口铁皮上清楚地编写号码” 。又如,通过发放“夜行执照”的方式控制夜间行人,通过发放牌照加强对租界内的赌场、烟馆和妓院的管理等。在各种管理措施的执行过程中,罪与罚是否适当是租界与华界双方在城市治安管理中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又如,通过发放“夜行执照”的方式控制夜间行人,通过发放牌照加强对租界内的赌场、烟馆和妓院的管理等。在各种管理措施的执行过程中,罪与罚是否适当是租界与华界双方在城市治安管理中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租界当局判处华人罪犯苦役为例。1856年7月,在租界董事会会议中,“罗伯逊先生告诉董事会说,为了避免麻烦而又要保证处罚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他已征得‘知县’的许可,把带到他面前来的华人罪犯判处或轻或重的筑路劳动,同时为了安全防范起见,用铁链把他们一组一组连锁在一起,但我们要供应他们食物” 。租界当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清官员在惩罚交给他们的囚犯时量刑不当,有的罪犯甚至“可以花钱逃避处罚”。他们抱怨说:“到目前为止,困难不是在逮捕这些罪犯,而是确定他们有罪之后如何给以令人满意的惩处。”
。租界当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清官员在惩罚交给他们的囚犯时量刑不当,有的罪犯甚至“可以花钱逃避处罚”。他们抱怨说:“到目前为止,困难不是在逮捕这些罪犯,而是确定他们有罪之后如何给以令人满意的惩处。” 于是租界当局决定判处在租界行窃的华人服苦役。“据工部局统计,一八六五年九月间,法庭所审轻犯罪人共一七九人,其中经判处苦工者为三五人,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到十月间,犯人共二一七人,经判苦工者达七五人,竟占三分之一以上。”
于是租界当局决定判处在租界行窃的华人服苦役。“据工部局统计,一八六五年九月间,法庭所审轻犯罪人共一七九人,其中经判处苦工者为三五人,占全数五分之一弱。而到十月间,犯人共二一七人,经判苦工者达七五人,竟占三分之一以上。”
苦役犯刑期从3天到3个月不等,主要从事租界内的市政工程建设,包括砸石子、筑路等。在从事苦役劳动时,苦役犯往往被在腰部用铁链环扣,数人栓系在一起。
姑且不论租界当局的这种做法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即以这一惩罚本身是轻是重而言,爆发于因犯人戴中其在服苦役时不幸死亡引起的中外交涉,就体现了中外在刑与罚方面的区别。因为用60个铜钱购买赃物——一把门锁,戴中其被判处服两个月的苦役。戴中其“身体虚弱,无力干活,而且主管巡捕经常推他、拖他和打他。这种虐待持续了好几天,而且天气又是刮风,又是下雨”,戴中其在被送往医院后死了。
上海道台在致英国领事的函件中说:“假如戴中其不知道他购买的财物是赃物,那么根据中国的法律,就不会认为他是有罪的;假如他知道的话,但由于这是一件不值几个铜钱的小东西,惩罚将是很轻的。”而租界当局让戴中其等犯人干“包括开沟、敲石子、修路筑路、挖河泥填到岸上等类活;犯人被铁链锁在一起,二三十个人一组,主管巡捕对他们很凶狠,假如犯人因劳累歇一歇,或者没有听懂意思,主管巡捕就向他们挥舞木棍。不管雨下得多大,也不得停工。就吃的而言,一日三餐,每顿一小碗冷饭,只有到晚上才喝到一点凉水。这种待遇比上枷还严厉” 。因此要求英国领事干预租界当局,停止苦役处罚。
。因此要求英国领事干预租界当局,停止苦役处罚。
工部局在写给英国领事的回函中认为:“对可能停止中国犯人实施这种有益的苦役刑罚感到遗憾,因为在真正实施这种惩罚的有限时间内,其好处日见明显。罪犯现在知道犯了罪就会受到真正的刑罚,他看到其他人正在受到这种惩罚,因此,感到犯了法不会像以前那样仅仅‘送进县城’,到了理事衙门,也不会被释放,而可能不得不真的去干苦活。接受赃物的人以及对租界内的居民进行敲诈或‘勒索’的人现在感到他们的这种行径更危险了,因为不是被‘送进县城’,行贿一下就被释放,他们害怕被用铁链锁在一起。”
显然租界当局认为,处以苦役之惩罚对这些人来说是最为适当的,正是苦役使这类人犯罪成本提高,从而不敢犯罪。而事实上也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因为“自从开始实施这种刑罚以来,犯罪率明显下降。广东和福建无赖正在迅速离开。督察员认为,用铁链把犯人锁在一起的方法比十多名巡捕更能有效地制止犯罪” 。因此“抑制租界内犯罪率好处无量,要做到这一点,苦役刑显得十分有效”。他们进而认为“有争议的不是服不服苦役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剥夺那些贪污腐化官员和县衙门食客非法勒索租界内居民钱财权力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此”
。因此“抑制租界内犯罪率好处无量,要做到这一点,苦役刑显得十分有效”。他们进而认为“有争议的不是服不服苦役这个简单的问题,而是剥夺那些贪污腐化官员和县衙门食客非法勒索租界内居民钱财权力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此” 。
。
就上述争论来说,不论租界当局是否有处罚中国居民的权力,亦不论苦役刑罚是否真的对租界犯罪率的下降产生了何等影响,就事情本身而言,是中外因罪与罚是否得当而引起的争论。在我们的法律理念中,尽管同样有判处罪犯服劳役的规定, 但是在中国当局的眼里,像戴中其这种犯罪实属轻微细故,处罚最多是“枷号”一定时间。而在外国人看来,偷窃、勒索对租界社会治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治乱世用重典,应当加重对这类犯罪的处罚,因而认为处罚是适当的。
但是在中国当局的眼里,像戴中其这种犯罪实属轻微细故,处罚最多是“枷号”一定时间。而在外国人看来,偷窃、勒索对租界社会治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治乱世用重典,应当加重对这类犯罪的处罚,因而认为处罚是适当的。
根据中英双方的交涉,工部局于1866年初制定了《苦役犯人惩处规则》,主要内容有:只有犯有抢劫、偷盗、窝脏、勒索等罪行的犯人才可处以苦役,其他罪行判处苦役应首先经过上海道台的同意;所有苦役犯人的情况应随时向上海道台呈报;凡是18岁以下、45岁以上的男犯及女犯不得处以苦役;苦役犯的劳动时间为夏季上午6—10时,下午4—6时,冬季上午10时—下午4时;巡士不得殴打虐待犯人。 后来在中方的压力下,1870年3月31日,苦役制度被废除。
后来在中方的压力下,1870年3月31日,苦役制度被废除。
开埠后的上海,同一城市中存在着租界、华界;同样在租界内,华洋混杂。在双方各自存在、和谐共处之外,中外之交锋、冲突亦是深刻的和不可避免的。这种交锋涉及从思想到文化,从习惯到观念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以前我们比较多地注意到西方物质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于物质文明的交锋,卢汉超先生在种种罗列后总结道:“……凡此种种,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它们不像当时的中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那样对照强烈,令人触目惊心,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确乎微弱得多,但物质的东西对于人们的观念却有一种难以抗扼的潜移默化作用。” 而实际上,除了物质文明、意识形态的交锋以外,在城市管理理念方面,上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外交锋的平台。
而实际上,除了物质文明、意识形态的交锋以外,在城市管理理念方面,上海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外交锋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