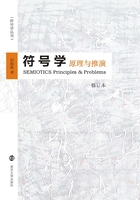
4.无限衍义,分岔衍义
皮尔斯对解释项有更进一步的解释。符号“面对另一个人,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心中创造一个相应的,或进一步发展的符号”。他的意思是,符号必须有接收者(是否必须是“另一个人”,本书第二章第七节“自我符号”已有讨论),在接收者心里,每个解释项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再现体,构成无尽头的一系列相继的解释项。“一个符号,或称一个表现体,对于某人来说在某个方面或某个品格上代替某事物。该符号在此人心中唤起一个等同的或更发展的符号,由该符号创造的此符号,我们称为解释项。”(28)这个理解非常出色:解释项是意义,但它必然是一个新的符号,因为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再现。
由此,皮尔斯给符号一个绝妙的悖论式定义:“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以至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29)这段话似乎绕口,却非常值得细细思考。要说明一个解释项,必须开始另一个符号过程,符号的意义必然是“可解释的”(见第二章第三节),但是要解释意义,就必须另用一个符号。
这样一来,符号过程,定义上不可能终结,因为解释符号的符号依然需要另一个符号来解释。皮尔斯理论比索绪尔的开阔,正是由于从解释项推出的这个“无限衍义”(infinite semiosis,艾柯称为unlimited semiosis)概念令人惊奇地预示了后结构主义的开放姿态:符号表意,必然是无限衍义。
让我试用平易的语言来解释一遍皮尔斯这个重要概念:
1.符号指向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象,另一个是解释项。
2.解释项是“指涉同一对象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解释项要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达。
3.而这个新的符号表意又会产生另一个解释项,如此绵延以至无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一个符号的意义。
对象是符号文本直接指明的部分,而解释项是需要再次解释,从而不断延展的部分。解释项不仅是能够延伸到另一个符号过程,解释项必须用另一个符号才能表现自己。这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本身就是无限衍义的过程,不用衍义就无法讨论意义,意义本身就是衍义,因此,符号学本质上是动力性的。
皮尔斯自己明白解释项/无限衍义这个理解方式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无限衍义是人的思想方式的本质特征,“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思想说话”。“思想永远用对话的形式进展——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这样,对话性(dialogical)本质上就是由符号组成。”(30)不管是与他人思想对话,还是与自己的思想对话,符号意义只有在对抗与衍生中才真正成为意义。
皮尔斯并不知道索绪尔与他同时在创建另一种符号学模式,但他似乎处处有意用他的符号三元原则来对抗索绪尔的二元原则,而且似乎明白这种对抗可能导致的巨大分歧:“一个只有三条分叉的路可以有任何数量的终点,而一端接一端的直线的路只能产生两个终点,因此,任何数字,无论多大,都可以在三种事物的组合基础上产生。”(31)三元组成,保证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发展开放,也让我们想起了老子的名言“三生万物”。
索绪尔式的符号学走向系统观,主要原因是索绪尔的符号意义“任意性”。二元式本身并不必然会导向封闭,例如叶尔姆斯列夫与巴尔特都在能指/所指二元式基础上提出过进一步衍义的梯级方式。(32)但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性,不仅在于用“理据性”代替任意性,不仅在于一系列三元式,更在于皮尔斯强调坚持无限衍义原则。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是无结束的,在实践中,表意“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33)。
这个讨论可能抽象,却很容易理解。例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表意例子“树的称呼树”,而一旦置入皮尔斯的无限衍义,就会演变开来:

哪怕“树”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我们的解释也永远不会终止。虽然在具体的符号表意中,意义解释因为各种实际原因,会暂时终止于某一点,但衍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衍生的必要性也一直存在。
任何符号都可以引向无限衍义,包括最原始文化中的符号表意过程中。人类学家列维-布吕艾尔(Lucien Lévy-Brühl)举过一个例子:“一片树叶上有个脚印指示了有个人踩在上面,脚印的方向影响踩着树叶的人,这个人又象征了他所属的部落。”这就开始了一个无限衍义过程。(34)
皮尔斯为无限衍义提出一段更诗意的说明:“人指向(denote)此刻他注意力所在的对象;人却意味(connote)他对此对象的知识和感觉,他本人正是这种形式或知识类别的肉体化身(incarnation);他的解释项即此认知的未来记忆,他本人的未来,他表达意义的另一个人,或是他写下的句子,或是他生下的孩子。”(35)解释项是符号生命延续,就像某些东西是人的生命延续。

人的生命,人的存在,人类的繁衍,就是符号的无限衍义。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理解。我们想起皮尔斯主张“人本身是符号”,这个惊人的看法,一旦无限衍义,就演化成“人的世世代代”是符号过程。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孩子,都可以是“符号自我”的延伸。
敏感的读者想必已经发现,我们能从皮尔斯的无限衍义思想中,找到通向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后结构主义思想的门径。符号学家科尔比指出,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还预言了八十年代后结构主义的一系列观念:博尔赫斯的“迷宫”、艾柯的“百科全书”、德勒兹的“块茎传播”、互联网之“万维”等等。(36)
艾柯在无限衍义基础上提出“封闭漂流”(Hermetic Drift)概念。他认为符号衍义是不必追溯的。假定衍义已经从A到E,“最终能是A与E连接的只有一点:他们都从属于一个家族像似网络……但是在这个链条中,一旦我们认识E时,关于A的想法已经消失。内涵扩散就像癌症,每一步,前一个符号就忘记了,消除了,漂流的快乐在于从符号漂流到符号,除了在符号与物的迷宫中游荡其他没有目的”(37)。艾柯的意思是无限衍义并不是同一个符号的累加解释,而是不断更换成新的符号。至少,这是无限衍义的变体之一:已经过去的衍义过程,有可能已经没有痕迹。
可以用博德利亚对当代媒体的批评来说明“封闭漂流”理论。一旦事件进入传媒,传媒就按“拟像”的四个阶段延伸。第一阶段,媒体介入零度事件;第二阶段,将其变成媒体事件,同时将其抽象化为信息;第三阶段,若干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形成若干媒体事件,在角度、方法、内容等不同技术手段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事件,越来越多信息的出现,只是为了掩盖事件退出这一个事实;第四阶段:媒体与事件已经不再有联系,它只是自身的拟像。媒体信息互相指涉,而不指涉事件。(38)试说明如下:
(1)“零度事件”就是“表现体”,尚无意义可言,此谓“零度”。
(2)“媒体事件”就是符号文本。
(3)媒体大量加入,解释其意义,意义使“事件退出”。
(4)媒体的报道衍生出报道,无限衍义以至无穷,与衍义起因的联系就不很明显。
所以,博德利亚声称“作为事件的海湾战争从未发生过”,这场战争是一个媒体上的战争,是一个巨大的拟像。(39)
这是可能,但不一定是必然。我们都是祖先无限衍义的后果,可能已经不难以追寻这个过程,E点已经不了解A点,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前辈留下的,我们无法摆脱文化传承,因此衍义过程不一定毫无痕迹。
无限衍义一直发展下去,最后会达到怎样一种境地呢?皮尔斯认为:“正由于解释会成为一种符号,所以可能需要一种补充性解释,它和已经扩充过的符号一起,构成更大的符号;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下去,我们将会,或者说应当会最终触及符号本身。”(40)这种最后的“符号本身”究竟是什么?艾柯解释说这个“最终符号实际上不是符号,而是结构那样的把混合性衔接并联系起来的整体语意场”(41)。 所谓“整体语意场”就是文化。一个符号的无限衍义,最后可能延及整个文化。
在符号的实践中,这是不可能的,不然每个符号过程最终会殊途同归。符号表意与无限衍义,两者同义,因为理论上没有“有限表意”;两者又不同义,因为任何符号表意活动都会中止在某处,潜在符号甚至从来没有开始。大部分符号由于解释过程中的实际原因——接收者的能力,解释意愿,或者简单地因为时间不够——总会停止于某些意义的积累点上,暂时不再延伸下去。任何解释活动,由解释意图推动。当这个意图消失,解释者已经满足于一种取得的意义,意义推演就暂时停止,此时无限衍义就变成一种潜在可能。
而且,显然存在“分岔衍义”:不仅是解释项产生另一个符号,同一个符号可以产生不同的解释项。例如皮尔斯说的“人生意义”的解释项,就可以是“未来、他人、写作、孩子”四种。此种平行式的意义衍生,更加剧了符号意义的流散。分岔衍义,是接收者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鲁迅那段各种人读《红楼梦》的名言,很多人引用。每一个解释都可以衍生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红学”。
即使同一个解释者,也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心态下,在同一符号中也会读出不同意义,也会朝着不同方向延伸。例如近几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大多数倾向于题目模糊,允许学生分岔衍义,考生发展自己的论述余地较大。2009年北京考场用了台湾女歌手张韶涵的歌《隐形的翅膀》,虽然题解给了一段歌词,有人指出这是“小女生的歌”,男生不太熟,不得不让衍义朝不同的分岔方向走。
分岔衍义也给误读提供了机会,只要第一环节似乎有根据,以下的衍义就都似乎是有道理。例如费诺罗萨学习中国诗的笔记中,记下了一些关于汉字的说法,被美国诗人庞德抓住了,以此为根据构筑了一套“表意文字法”(Ideogrammic Method)体系,给美国现代诗提供了“整整一套价值观”。(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