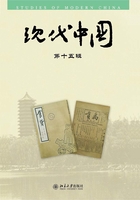
余论
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十月间,叶瀚、汪锺霖、汪康年、曾广铨等趋新人士在上海设立蒙学公会,继而创办《蒙学报》,着手筹备新式蒙学堂。梁启超为撰《蒙学报演义报合叙》,将西洋、日本教科书的发达归结于游戏小说、俚歌的流行,继而将《蒙学报》与其门人所办之《演义报》相提并论。[149]与此同时,马良致信汪康年,亦提到《蒙学报》《演义报》合二为一的设想。[150]可见,在戊戌年变法维新高潮到来的前夕,语言文字论与蒙学变革论同时高涨、互相影响,时人也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反而是后来人在追溯时,出于各自的言说动机与学科分野,往往偏于一端。
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批复卢戆章所呈《切音新字》,提到:“文字之难易,又复与教化之广狭相为比例:识字难,则游惰不得不多;识字易,则教育自然普及。”[151]字学难易与教育普及的关系,最终得到官方确认。然而,当年“字学”论说潮流中颇为抢眼的切音文字论,落实到蒙学变革的言论及实践,却相对较为弱势。从整个清末教育改革、学制制定的过程来看,戊戌以前的切音字方案始终被排除在正则学制之外;即便后来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凭借官方力量得到推广,亦仅适用于下层启蒙或变则教育。对照之下,以官话为基准的各种白话、浅说、“演义”,由于在传统启蒙教育中渊源有自[152],不仅更容易与教学实践相磨合,更对此后蒙学读本乃至“国文教科书”文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
本文关注甲午、戊戌之间蒙学新论致力于语言文字的侧面,更注意到:正是教育普及观念下“识字作文”能力的突出,使得新式蒙学有以区别于(梁启超等塑造的)以经训诵读为先的旧蒙学形象,从而为接引新学制下的中小学“国文”教育奠定了基础。相关论述更多侧重于言论而非实践。《蒙学报》发端于丁酉秋冬之际,受到梁启超《幼学》篇启发,当然亦可视作戊戌前夜蒙学变革论的展开;在其试编识字作文用书的过程中,蒙学新论与同时期语文论说的对话更是显而易见。然而,《蒙学报》并不属于《时务报》一系言论主打的刊物,其重点在于蒙学用书的按期发布,而非教育新论的阐述。更重要的是,《蒙学报》的发行跨越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大难关,一直持续到庚(1900)、辛(1901)之际新政重启之时。作为清末新式读本、教科书的前驱,《蒙学报》的影响已及于酝酿学制的时期,其所取法亦已超出戊戌前论者借重的西方资源。姑且在此按下不表,留待另文处理。[153]
2012年5月9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1] 本稿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清末‘国文’的兴起:学科、文体与文化认同的互动”(项目编号:2012M520092)的阶段性成果。
[2] 陈荣衮:《论训蒙宜先解字》(光绪二十五年[1899]),区朗若、冼玉清、陈德芸编校:《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3a—4a叶,广州子褒学校同学会1953年铅印本。
[3] 陈荣衮后撰《论训蒙宜用浅白读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即指出:“四书五经之道理,无分古今,惟其语言则儒林古国之语,而非今国之语也。若以今国之语言写无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见前揭《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11b叶。
[4] 参见杞庐主人编:《时务通考》卷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257册影印上海点石斋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第567—578页;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五,上海宝善斋光绪二十七年(1901)石印本。
[5] 戊戌时期康、梁一派多强调“官制”,如《变法当知本原说》(《强学报》第2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三日)及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二)》(《时务报》第3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二十一日)、麦孟华《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时务报》第22、24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一日、二十一日)等文,均认为变官制为万事根本,对戊戌年出自朝廷的维新政策多有影响。
[6] 参见汪康年:《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时务报》第11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7] 参见福开森(John C. Ferguson,1866—1945):《强华本源论》,《万国公报》(月刊)第93卷,光绪二十二年八月。
[8] 参见梁启超:《论学校一:总论(变法通议三之一)》,《时务报》第5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9] 参见渤海姜叔子:《改正朔易服色说》,《万国公报》(月刊)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
[10]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第1—7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
[11] 卢戆章:《变通推原说》、《变通推原第二章》、《三续变通推原说》、《四续变通推原说》,分别载《万国公报》(月刊)第78、81、82、86卷,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九月、十月,二十二年正月。
[12] 分别为:卢戆章的“切音新字”(1892)、吴脁的“豆芽字母”(1895)、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天下公字”(1896)、力捷三的“闽腔快字”(1896)、康有为嘱其女编纂的音字(1896前)、王炳耀的“拼音字谱”(1897前)。参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方案一览表》,《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第9—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13] 吴沈学来稿:《附盛世元音原序》,《时务报》第4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一日。
[14]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合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
[15] 陈荣衮:《论报章宜用浅说》(光绪二十五年),《陈子褒先生教育遗集》,第5b—9b叶。
[16] 阙名:《论中国文章首宜变革》,《亚东时报》第7号,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十日。
[17] 王树枏:《致何善孙(戊戌)》其十,《陶庐笺牍》卷四,光绪戊申(1908)刊本。
[18] 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万国公报》(月刊)第86卷,光绪二十二年正月。
[19] 吴沈学来稿:《盛世元音原序》《体用》,《时务报》第4、12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一日、十月二十一日。
[20] 卢戆章曾应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的邀请,助译《华英字典》,其“切音新字”方案实际上参照了当时的“厦门话教会罗马字”;沈学则原为上海的教会学校梵皇渡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的医学生,精通英文。相关生平考论,参见前揭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第19—20、41页。
[21] 花之安:《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年铅印本,第19—21叶(卷叶);《自西徂东·同文要学》,《万国公报》(周刊)第727卷,光绪九年正月十日。按:花之安提出用“夹音”之法厘正方言,前提仍是“正音”:“如粤东则以羊城为正,福建则以榕城为正,中国则以正音为正。……国家著为功令,则易遵矣。”实际上并未解决拼音化与语言统一的冲突。见《教化议》,第20叶(卷叶)。
[22] 如后来被看作守旧的叶德辉,在戊戌年(1898)所作《非〈幼学通议〉》中即提到:“曩于花之安《【泰西】学校》、《教化议》得知其详,其议论是己非人,如以中文为板文,满洲书西域书为胶漆话之类,大都逞其私见,不究本原。”见苏舆编:《翼教丛编》卷四,第13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23]都戈拉斯著、古吴居士(沈毓桂)笔述:《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万国公报》(月刊)第52卷,光绪十九年四月。原书为R. K. Douglas,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May and June,1875年由伦敦Trübner and Co.出版社刊行。
[24] 参见利玛窦:《论耶稣会及基督教进入中国》,转引自卡萨齐(G. Casacchia)、莎丽达(M. Gianninoto):《汉语流传欧洲史》,第8、1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年。
[25] 郭嵩焘:《使西记程》,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廿四日条下,见钟叔河编校:《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
[26]潘慎文:《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及大学中的地位》,原载《在华传教士1890年大会纪录》,译文转引自朱有 、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127—12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127—12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27]如Elisabeth Kaske在概述晚清来自教会的拼音方案与翻译《圣经》的文体争论时,即指出:“非常明显的是,在传教士当中并没有能够产生足以引领中国自身发展的一致并且积极的语言方针。毋宁说,传教士们是根据中国自身的语言状况来反应,直到变化发生以后(通常有一个时间差),才开始调整他们的语言方针。”见Elisabeth Kaske,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1895-1919,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08,p.65。
[28] 见杨毓煇:《华人讲求西学用华文用西文利弊若何论》,王韬鉴定:《格致书院课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富强斋书局石印本,西学类,第1a—5a叶(卷叶)。按,该文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获格致书院己丑冬季课题超等第一名。后改题《中西书法异同论》,收入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卷四十二。
[29]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原书》(光绪十四、十五年间[1888—89]作),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5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0] 如名列该次课艺“超等第二名”的沈尚功即指出:“以中国人读中国字,而高下徐疾即各自成音,赖有象形、会意等义相维持。故数千年后,犹得以考证古训也。西国文字,仅知协声,以口相传,久而异变,安能如华文之六体兼备,如四声勿乱哉?”见前揭《格致书院课艺》,字学类,第6b叶(卷叶)。
[31]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第3b—7a叶(卷叶),光绪十六年(1890)羊城富文斋刊本。
[32] 《日本国志》卷三十三,第4a叶(卷叶)。粗体为笔者所加。
[33]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时务报》第4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一日。
[34] 如叶瀚《蒙学报缘起》化用此段,即以之来说明中国童蒙识字的困难:“有一字而兼数音,一音而备数义,综举则词繁,略之则义阙,此识字之难一也。”见《蒙学报》第1册卷首,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日。
[35]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第31—32页。
[36] 根据汤志钧的考证,康有为自称撰于光绪甲申(1884)的《大同书》,实际成书于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1901—1902)间,此后又屡经修改。参见汤志钧:《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第108—1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7] 康有为:《教学通议·言语第二十九》,载前《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4—56页。
[38]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幼学》篇则直接提到“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分别参见《时务报》第4、16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一日、十二月一日。稍后,裘廷梁撰《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亦以为“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并举五帝、三王时代著书、文告皆白话为例。
[39] 如后来黎锦熙就从“国语运动史”的角度指出:“当国语运动的第一期,那些运动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国语统一这个口号,乃是到了第二期才叫出来的。”见黎锦熙:《国语运动》,第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40] 《教学通议·言语第二十九》,《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4页。
[41] 康有为:《笔记·文章》,《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07页。《康有为全集》编者推定此篇作于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似可从。
[42] 关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讲述“文章源流”,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与阐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153—1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3] 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万国公报》(月刊)第86卷,光绪二十二年正月。
[44] 沈学:《盛世元音原序》,《时务报》第4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一日。
[45] 与梁启超同在康有为门下的陈荣衮即曾批评梁启超的“文质两存说”:“今之君子,有为文质两存之说者,亦非计之得也。假如出一段言语,十人中有五人知之,有五人不知,孰若出一段言语,十人闻之即有十人知之也。”参见前揭陈荣衮:《论报章宜用浅说》,《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9b页。
[46] 李提摩太:《宜习英文说》,《时事新论》卷八,第13a叶,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广学会铅印本。粗体为笔者所加。
[47] 郑观应:《华人宜通西文说》,《盛世危言(十四卷本)·西学》附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283—2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48] 李提摩太、郑观应的议论重点仍在西文,但当时亦无不从偏袒汉字的反方向宣扬“汉文精深”与“西文简易”不妨并存的论调。如《时务通论》即有“西国文字简易”一条,认为西文“语言即文字,简易易知,顾其为书,便于直陈器数,难于曲达义理。举国聪明才智,注于器数,故日进富强;无深至之文言,则性情不感,而日趋诈利”;相比之下,“中文主形,形中见义,所谓圣人见分理可相别异,故制文字。西人无分理之别,先不能立纲常之名,故不知有名教”。尽管有此“诈力”与“名教”之别,但寰球大势趋于功利,则又不得不习西文。见《时务通论》卷十九,前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74—575页。
[49] 《变通推原说·本馆附志》,《万国公报》(月刊)第78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
[50] 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万国公报》(月刊)第86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
[51] 沈学:《附盛世元音原序》,《时务报》第4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一日。
[52]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期合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
[53] 马建忠:《后序》,《马氏文通》,卷首后序第2a—2b叶,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孟冬铅印本。粗体为笔者所加。
[54] 马建忠:《后序》,《马氏文通》,卷首后序第2a叶,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孟冬铅印本。粗体为笔者所加。
[55] 郑观应:《复蔡毅若观察书》,前揭《郑观应集》下卷,第201—202页。信中提到王炳耀、沈学的切音字方案,则至少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以后;而蔡锡勇又卒于光绪二十三年,故推论在此二年之间。
[56] 代表性的反响,如郑荣:《读新会梁氏论幼学书后》,《湘报》第54号,光绪二十三年(1897)闰三月十七日;从反面加以驳斥的,则有叶德辉:《非〈幼学通议〉》,作于戊戌年(1898)秋。叶德辉的驳论,主要循着七类蒙学新书的结构展开,即便反对梁启超的议论,却在无意中接受了其框架。见前揭《翼教丛编》卷四,第130—137页。
[57] 梁启超:《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连载于《时务报》第16—19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十一日、二月初一日。按,该文收入丛书或文集时,曾被改题《幼学通议》《论幼学》等。本文征引根据原出处,一律称为《幼学》篇。
[58] 康有为万木草堂讲学,曾以“魂”“魄”之别区分孟子、荀子的性说:“荀子言性以魄言之,孟子言性以魂言之,皆不能备。”又说:“学者能以魂治魄,君子也;若以魄夺魂,小人也。”已经在二者之间作出了“魂”优先于“魄”的判断。至于“孺子有魄无魂,故无知识”之说,更是将“魂”视为获得“知识”的首要条件。见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荀子》,《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86页。而梁启超在给严复的回信中则指出:“以魂、魄属大小囱之论,闻诸穗卿(夏曾佑)。”见《与严又陵先生书》(丁酉春),见前揭《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106页。
[59] 花之安在《教化议》中指出:“开蒙便授以《三字经》,言性理,再则读《学》、《庸》,言修齐治平之法,参赞化育之功。此等之道,岂初学所能辨乎?”见前揭《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第19叶(卷叶)。
[60] 花之安:《教化议》,前揭《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第19叶(卷叶)。
[61]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周刊)第653卷,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三日。该文前半部分,又曾以《论学问之益原无限量》为题,重刊于《万国公报》(月刊)第52卷,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
[62] 关于狄考文对梁启超的影响,参见村尾进:《万木森々:『时务报』时期の梁启超とその周边》,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第54—55页,みすず书房,1999年。
[63] 林乐知:《险语对》(下之中),蔡尔康译,《万国公报》(月刊)第87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粗体为笔者所加。
[64] 前揭《教化议》,《泰西学校、教化议合刻》,第19—20叶。
[65] 前揭狄考文:《振兴学校论》。
[66] 梁启超:《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时务报》第17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67] 梁启超在《幼学》篇中即指出:“其诵经也,试题之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来耳。”又说:“近世之专以记诵教人者,亦有故焉,彼其读书固为科第也,诵经固为题目也。……故窒脑之祸,自考试始。”可见其纸背的用意。见《时务报》第16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68] 张伯行辑录:《陆桴亭论小学》,见张伯行编:《养正类编》卷二,《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影印同治五年(1866)夏月福州正谊书局刻本,第301页上栏。
[69] 郑观应在《答潘均笙先生论学校书》中,即全文照录陆世仪此段。见前揭《郑观应集》下卷,第222页。
[70] 见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71] 《掌故书目提要·肄业要览一卷》,《湘学新报》第4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一日。
[72] 梁启超:《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时务报》第29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73] 夏晓虹:《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74] 梁启超:《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时务报》第18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梁氏还提到,顺德何穗田在澳门集款开办了幼学书局,拟先印行识字、文法、歌诀、问答四种,光绪二十三年(1897)夏间“即当脱稿”,由广时务报馆(知新报馆)印行;其名物一书亦已开编。
[75] 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序》,前揭《〈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17页。
[76] 参见康有为:《教学通议·公学第三》,《康有为全集》第1卷,第21页。
[77] 康有为:《论幼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9—60页。
[78] 关于此趋向,可参考《义学规则十八条》及《变通小学义塾章程·义塾条规》等材料,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卷》,第347、35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
[79] 杨寿昌:《序》,前揭《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卷首。但同书卷末的《陈子褒先生编著书目》则将该书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
[80] 陈荣衮:《妇孺须知》,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无统一页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81] 陈荣衮《〈幼雅〉自序》明确指出:“南海先生惄然忞之,命撰《幼雅》。”见《幼雅》卷首,光绪丁酉(1897)羊城崇兰仙馆刊本。感谢李婉薇学长惠赐此书图版。
[82] 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引自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第233—23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粗体为笔者所加。
[83]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十,“教育门·小学读本挂图”类识语,《康有为全集》第3卷,第409页。值得注意的是,史家早已指出李端棻所奏很可能由梁启超代拟;因此整个蒙学新书目的计划,说是起于李端棻的推广学堂折,亦有可能即是康、梁早已有之的筹划。关于李端棻奏折的作者,参见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8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十,《康有为全集》第3卷,第409—410页。
[85] 必须指出,梁启超《幼学》篇未出现有关切音文字的内容,可能是因为《变法通议·论学校》的整体框架中原另有“文字”一篇的设计,故而在此省略。参见《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时务报》第6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二十一日。
[86] 《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时务报》第19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一日。
[87] 当然,康有为的“名物”类本身亦含有识字的内容,与梁启超直接字典、百科全书的“名物书”尚有不同。因此二者排序的分歧亦不能过分夸张,大体上仍是以识字教育为先。
[88] 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第223页。
[89] 见前揭《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42页。
[90]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时务报》第4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廿一日。该篇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二,“三十人”变为“二十人”;根据下引《幼学》篇开头的数据,自以《时务报》初刊为正。
[91] 见《时务报》第16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92] 李提摩太《论学人》提到:“中国年已长成之人,无论男女贵贱,统计入学肄业读书识字者,每百人中仅有十一人。……即推而广之,以中国之能识之无者充类并计,每百人中作二十人,较之西国亦只有三分之一耳。”与梁启超《幼学》篇的措辞尤为接近。而《论学校》则指出:“中国十八省生齿日繁,统计每百人中能识字记事者约不过十余人。”康、梁大致是在其基础上,选择了比较多的数字。见前揭《时事新论》卷八,第1b、2b页。
[93] 见前揭《沈氏音书序》。
[94] 茅谦:《变通小学议》(丁酉[1897]五月稿),《皇朝蓄艾文编》卷十五,第2a—4b叶(卷叶),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官书局铅印本。
[95] 裘廷梁:《致汪康年》二,《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625—26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6] 在《文字蒙求》一书的原序中,王筠借好友陈山嵋的话指出:“苟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总四者而约计之,亦不过二千字而尽。当小儿四五岁时,识此二千字非难事也,而于全部《说文》九千余字,固已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矣。”这些观点,均在梁启超《幼学》篇“识字书”一段中有所体现。原序见王筠撰、蒯光典增注:《文字蒙求广义》卷首,江楚书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序刻本。
[97]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梁启超后来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忆及,《马氏文通》著于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1895—1896),马建忠“住在上海的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见夏晓虹等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第2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98] 叶德辉:《非〈幼学通议〉》,前揭《翼教丛编》卷四,第133—134页。
[99] 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第234页。
[100] 梁启超:《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时务报》第6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二十一日。
[101]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时务报》第44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一日。
[102] 梁启超:《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前揭《〈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35页。
[103] 参见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知新报》第3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丁酉冬),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二,第27页。
[104]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湘报》刊出“长沙任氏正蒙学堂学规”,即直接模仿了《幼学》篇的“功课表”;同年七月,《国闻报》刊布“长沙周会昌拟学堂公法”,亦基本上是按照《幼学》篇七种书的框架来设计其课程。可见《幼学》篇至少在康、梁一派势力活跃的长沙,仍有一定的影响力。分别参见《长沙任氏正蒙学堂学规》,《湘报》第102号,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六日;《学堂公法》,原载戊戌七月《国闻报》,转引自佗城倚剑生编:《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第660—662页,《中华文史丛书》影印光绪戊戌广州广智报局铅印本。
[105] 梁启超:《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时务报》第19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一日。
[106] 梁启超:《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时务报》第16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107]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清代之科举”条,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08] 梅鹤孙:《青谿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梅英超整理,第6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09] 参见梁启超:《三十自述》,前揭夏晓虹编校:《梁启超文选》上册,第364页。
[110] 这方面的专题研讨,参见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3页。近来更有学者指出,晚清以来所谓“私塾”,实际上是一个后起概念:“直至1905年科举停废前后,出于称谓排除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本土学塾的需要,新知识精英才普遍使用这一新词,且不为一般民众熟悉。”见左松涛:《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11] 唐彪:《父师善诱法》卷上,“经蒙宜分馆”条,《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合刻》,嘉庆八年(1803)敦化堂重刻本。
[112] 前揭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第37—41页。
[113] 专攻语文教育的张志公先生曾指出:“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工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参见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新探(附蒙学书目)》,第3—3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此处引自第3页。近年有学者通过比照清人年谱、日记等材料,认同张志公的估计有其可信度,参见前揭左松涛:《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
[114] 陈荣衮:《论训蒙宜先解字》,《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3a—4a叶。
[115] 叶德辉:《非〈幼学通议〉》,前揭《翼教丛编》卷四,第132页。
[116] 王筠:《教童子法》(不分卷),《灵鹣阁丛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
[117] 参见茅谦:《变通小学议》,前揭《皇朝蓄艾文编》卷十五,第3a叶(卷叶);陆基:《缓读四书五经说》,张一鹏辑:《便蒙丛书·教育文编》,苏州开智书室光绪壬寅年(1902)刻本,第1a叶(卷叶)。
[118] 张伯行辑:《朱子童蒙须知》,《养正类编》卷一,前揭《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影印本,第297页。
[119] 张伯行辑:《陆桴亭论小学》,《养正类编》卷二,第301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120] 唐彪:《父师善诱法》,卷下“童子最重识字并认字法”条、卷上“教法要务”条。
[121] 关于当时教会学校中文教学的状况,可参照热衷办学的传教士潘慎文在光绪十六年(1890)的描述:“有些地方,全部四书、五经列为中文课程,要求学生熟记,并练习写文章,准备参加政府考试;而另一些地方只教四书;有些学校只教四书,有些学校给学生一半的时间或更多的时间学习经书,而一些学校只给学生很少的一部分时间,总的来说是用次要的部分时间来学习经书。”可见教会学校教授中国学问采用的教法,至少是缺乏方向感的。见潘慎文:《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及大学中的地位》,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126—127页。又根据日文《上海新报》光绪十七年(1891)的观察,当时“上海没有合适的学校”,教会学校多以收容华人贫苦子弟为宗旨,并不适合居留外国人。参见《上海の諸学校》,原载东本愿寺编:《上海新报》第41号,1891年3月13日,转引自高西贤正编:《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资料篇第268页,东本愿寺上海别院,1937年。
[122]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致何树龄、徐勤的信中提到:“张经甫(焕纶)原我所举,其人笃实,与莲珊(经元善)至交,在城里梅溪书院。君勉(徐勤)亦可频入去(原注:易一[何树龄]亦宜入去),与之笔谈,彼必推服,甚要。”见《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200页。其《救时刍言》的主张,参见宋恕:《书张经甫〈救时刍言〉后》,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1—184页。
[123] 张在兴:《先君兴办梅溪学程事略》,《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7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24] 关于“申江雅集”,参见宋恕:《乙未日记摘要》,前揭《宋恕集》下册,第935页;钟镜芙:《钟鹤笙徵君年谱》,光绪二十二年(1896)条下,附载钟天纬:《刖足集》外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42册影印1933年铅印本,第774页。
[125] 陈三立:《钟徵君墓表》,《刖足集》外编,第768页。
[126] 钟天纬:《学堂宜用新法教授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82—584页。
[127] 钟天纬:《三等公学总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578—560页。但据薛毓良的考证,此章程出自三等公学成立以前,应题作《小学堂总章程》。参见薛毓良:《钟天纬传》,第252—25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
[128] 前揭《钟鹤笙徵君年谱》,《刖足集》外篇,第774页。
[129] 崔学古:《幼训》,王晫、张潮辑:《檀几丛书二集》卷八,第346—3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康熙三十四年(1695)新安张氏霞举堂刻本。
[130] 梁启超:《学校论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时务报》第19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一日。
[131] 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五彩精图方字》《五彩绘图看图识字》等识字玩具,“特制方字一千装入盒中,其先后以笔画之繁简、意义之浅深、音调之难易为准”;同时彪蒙书室亦有《五色绘图字块》出版,此类识字块到民国时代仍相当流行。参见《商务印书馆教育玩品》,《教育杂志》(商务)第1卷第1期附广告,宣统元年(1909)正月廿五日。
[132] 《二编编辑大意》,《新订蒙学课本》二编卷首,引自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2册,第526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33] 《蒙学读本全书四编约旨》,《大公报》第226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一日,“来稿代论”栏。
[134] 《义学章程》《粤东义塾规条》,原载《得一录》卷五,见前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卷》,第352、354、361页。
[135] 参见前揭薛毓良:《钟天纬传》,第148—152页。
[136] 喻长霖:《钟徵君传》,《刖足集》外篇,第768页。
[137] 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庆正蒙公塾所辑《正蒙字义》,即将钟天纬此种《字义》书视为传统字课书的一种而列为参考。其《凡例》有云:“是编意主适用,并求详备,多采魏默深(源)《蒙雅》、姜明夔《三千字文》、黄庆澄《训蒙捷径》、钟鹤笙(天纬)《读书乐》、吾乡潘氏季约《蒙雅纂要》、杜氏少瑶《课蒙举隅》诸书。”见《正蒙字义》卷首,光绪辛丑(1901)秋重庆正蒙公塾刻本。
[138] 钟天纬此书,以往教育史、出版史研究者多称为《字义教科书》,但该书原题仅“字义”二字。“字义教科书”之称,应是后来套用来自日本的“教科书”(きょうかしょ)这一新名词所致。《字义》一书实物传世极少,感谢江苏无锡的教科书收藏者王星示知相关情况。
[139] 《马氏文通》以前西人所撰中文语法书的概况,参见姚小平:《〈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语言文字学》1999年第9期。早期西人撰汉语语法书往往套用印欧语法框架,但到19世纪亦逐渐抛弃欧洲语法分类,转而采用中国自身的概念。关于此点,可参考前揭卡萨奇、莎莉达著《汉语流传欧洲史》第五章“明清以来欧洲人的汉语语法研究”,第91—157页。
[140] 沈学:《盛世元音·文学》,《时务报》第12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二十一日。
[141] 见《时务通考》卷十九,第568页,前揭《续修四库全书》第1257册影印本。
[142] 叶瀚:《中文释例》卷二,《蒙学报》第5册,笔者所见本未署出版时间,大致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
[143] 王季烈:《文法捷径》,《蒙学报》第23册,未署出版时间,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七日前后。
[144] 叶瀚:《初学宜读诸书要略·文法书》,《初学读书要略》,光绪丁酉(1897)夏仁和叶氏刻本。
[145] 东吴范祎:《国文之研究》,《寰球中国学生报》第2期,丙午(1906)七月。
[146] 《习对发蒙格式》,《缥缃对类大全》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6册影印明刻本,第652页。
[147]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48] 比如出自康门的陈荣衮就曾列举属对多种弊端,主张以“串字”(组词造句)取代属对,见陈荣衮:《学童串字说》(庚子),《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14a—15b叶。而直到三十余年后的1932年,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试题,仍引起轩然大波。关于此事件的专题讨论,可参见罗志田:《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第161—1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9]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时务报》第44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一日。
[150] 马良:《致汪康年》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九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569页。
[151] 学部编译局:《咨覆外务部卢戆章呈验所著字书文》(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五日),《学部官报》第1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初一日,“文牍”栏。
[152] 除了前引清初蒙学家的议论,民间流行的白话小说、戏曲、宣卷、弹词,尤其是对《圣谕广训》等官方文告的宣讲传统,对白话浅说文进入启蒙教育自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可参见夏晓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53] 参见拙文:《清末学制酝酿期“蒙学读本”的文体试验——以〈蒙学报〉为例》(未刊稿);《清末“蒙学读本”的文体意识与“国文”学科之建构》,《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