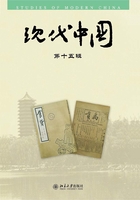
“旗营第一人才”
贵林先后担任过佐领与协领,无论哪一种职位,所管事务都限于驻防营之军事与政务。但他显然对此并不满足,于是,在浙江多项新政及社会团体中,都活跃着他的身影,并最终获得了旗营民意代表的资格。
尽管早在1889年,贵林已与宋恕建立友谊,1891年以前已经认识陈黻宸[29],不过,贵林之真正出名,广为人知,还在其1906年接手惠兴女学校之后。时人已有明言:“佐领贵林接办惠兴女学,一跃而为学界中有数人物。”[30]故讨论贵林在清末杭州以至浙江政局与社会上之影响,势必先从此说起。
惠兴与贵林一样,同为驻防营出身。其姓瓜尔佳氏,丈夫为镶蓝旗附生,早逝。[31]1904年10月24日,已经认识到“现在的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的惠兴,毅然“以提倡女学自任”,在杭州旗营中创办了贞文女学校。还在8月7日召开筹备会之际,惠兴即以满人刚毅的性格,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办学决心,当众割臂自誓曰:“今日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记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32]而学校开办一年后,因为在满人群体中得不到有力支持,艰难支撑的惠兴家产荡尽,最后于1905年12月21日于家中服毒自尽。临死前,惠兴留下遗书八封,并有上浙江将军瑞兴的禀帖,希望以自己的死,为贞文女校换取官方拨付的常年经费,也实践了其以身殉学的誓言。惠兴自杀后,其分别致以遗书、委托校务的两位旗人妇女均不肯接任,学校面临停顿。贵林及时施以援手,才使该女校获得了生机。
贵林对新式学堂的热心,早在1897年受命承办旗营中的梅青书院、大力购置新学书报上[33]已见一斑。其支持惠兴办学,先是推荐宋恕女儿宋昭到贞文女校任教,后又遵照惠兴遗嘱,将其请款禀帖转呈瑞兴,已可谓尽心尽力。尤其是在惠兴死后,贵林四处发送由他撰写的《杭州惠兴女士为兴女学殉身节略》,大力传扬惠兴为女学牺牲的事迹,其文不仅在《申报》得到刊载,并且感动了《北京女报》的主笔张毓书(字展云)。张氏一面在《北京女报》用白话倾心动情地演述惠兴故事,一面联络梆子戏著名演员田际云,及时编排出文明新戏《惠兴女士传》,于1906年3月29日开始在北京上演,此举借为贞文女学校募捐,而将兴办女学的思想普及到北方一般民众中。贵林也与之南北呼应,北京地区的大笔捐款保证了改名惠兴女学校的杭州旗营女校的再生,贵林也因其鼎力相助以及办学经验,被杭州驻防营公举承办该校,由瑞兴委派为总办。1907年5月,贵林进京,更直接参与了《惠兴女士传》的重演,在该戏临近尾声之处,张毓书邀请贵林登台,现身说法,报告观剧感想以及惠兴女校近况,使贵林的演说长才也得到了展示的机会。[34]而其议论诸葛亮著名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犹非上德者”,以为“当求死而不已”,既令孙宝瑄“深叹服”[35],也足以概括其将惠兴开创的事业继承维护并发扬光大的实绩。由此使得贵林在新学界声名鹊起。
不过,贵林的此番作为也不乏讥之为沽名钓誉者,从其本人的自述已可理会。1908年5月,贵林“为女学界联团体、便交通起见”[36],创办了《惠兴女学报》,发刊词中即道及:
中权受官、学二界之委托,感惠兴氏之激刺,由保守主义希望造时主义,至于今日,将及三年矣。凡此三年之间,除担任本校职任外,而他校以及公益、社会诸务,均就一己精力之所及,竭诚经营,不遗余力。誉者以为热心,毁者以为钓誉。中权氏不知其他,求心之所安,期事之有济。率此以往,即至牺牲己身,亦所不顾,矧区区毁誉乎?[37]
以此表明心迹,当然是信者自信,疑者仍疑。而贵林走出旗营,介入学界、商界、政界等各种社会群体的活动,其契机正在接办惠兴女学校,此段表白也提供了最有力的证言。
实际上,在旗营内部,贵林已努力推进多项改革。吴庆坻著《辛亥殉难记》称:“驻防营设学堂、办警察事并创举,独肩其劳。”[38]可见其大略。此外,1908年3月,贵林还在旗营自治会内发起组织了阅报社宣讲所,“定每月宣讲一次”,擅长演讲的贵林也当仁不让。[39]而依据《申报》的记述[40],1907年以后,贵林更频繁参与社会事务,可考知者如下:
1907年9月22日,参加浙江教育总会成立大会。
1907年11月14日,作为旗营学校代表,参加浙江学校认股会。
1907年11月25日,参加全省国民拒款大会,当选为杭(州)乍(浦)驻防代表。
1907年12月2日,作为驻防代表,参与全浙十一府暨驻防、留学界拒款会代表谒见新任浙江巡抚冯汝骙的请愿活动。
1907年12月9日,参加浙江教育总会正式大会,被推举为调查员。
1908年1月15日,参加浙江禁烟调查社新总理莅任欢迎会,发表演说。
1908年2月25日,参加在凤林寺举行的安葬秋瑾祭奠会,发表演说。
1908年6月29日,参加禁烟调查社周年纪念会,以社董身份报告入会理由,并代发起人辩诬。
1908年12月19日,参加浙江农工研究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副会长。
1909年3月6日,参加浙江省农务总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协理。
1909年9月12日,参加全浙保路会特别会,被推举为驻防代表,即任临时干事。
1909年9月25日,参加浙江省救火联合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临时议长,当选为副会长,以职繁辞。
1909年10月28日,以惠兴女学校校长身份,参加浙江教育总会举办的夏震武会长欢迎会。
1909年11月6日上午,参加全浙保路会及绅商学界为汤寿潜入觐举行的欢送大会;下午,参加浙江教育总会大会,当选为评议员。
1909年12月7日,参加全浙保路会举办的挽留汤寿潜、拒任江西提学使特别大会。
1910年1月2日,参加国民筹还国债大会,演说国民捐之历史。
1910年1月14日,以浙江省筹还国债会三位代表之一的身份,晋谒浙江巡抚增韫。
1910年1月23日,参加浙江省筹还国债会正式大会,被推举为学界八位代表之一,并发表演说。
1910年3月11日,参加杭嘉湖绍金衢严七府出品展览会开幕第一日活动,以来宾身份发表演说。
1910年3月20日,参加杭嘉湖绍等七府出品展览会开幕礼,以来宾身份发表演说。
1910年4月12日,担任浙江省第四次国会请愿代表选举大会主席,并作报告。
1910年7月24日,参加杭州商务总会邀集绅商学界讨论迁移日人商店后续问题之聚会,发言质询。
1910年9月9日,参加杭州士绅组织之浙路维持会会议,被推举为两名赴沪代表之一。
1910年9月10日,参加浙路维持会成立大会,发表意见。
1910年10月1日,担任全浙商会维持浙路大会主席,宣告意见。
1911年9月17日,参加浙江省水灾急赈会,发表意见。[41]
以上列出的27次活动尽管并不齐全,仍可看出贵林之勇于任事,且职务繁多。最忙的时候,他甚至一日之间,上、下午分别参加不同的会议。与会的种类也五花八门,大致确如其所说,可归纳为“公益、社会诸务”。个别组织固有官方色彩,如禁烟调查社总理,“向举臬司及巡警总办充任”[42],贵林本人也曾以巡抚代理委员的官家身份出席1909年10月14日举行的浙江谘议局成立大会[43],然而,其间民间社团占了绝大多数,也一目了然。
所有各项事务中,贵林参与最多、表现也最为突出的是浙江拒款保路运动。根据朱福诜等浙路全体股东代表1910年撰写的《浙江铁路始末述略》[44]记载,此一风潮起自1905年美商欲承办浙赣铁路,“浙人以保国权为念,群起力争”,于当年7月成立了商办全浙铁路公司,公举汤寿潜任总理,获得朝廷批准,由此开始民间的集款筑路。然而,早在1898年,清廷先已与英国银公司签订了包括苏杭甬(后改为沪杭甬)铁路在内的五条铁路修筑草约,英商据此要求正式签约,以借款的方式谋求控制路权。浙江全省由此兴起了国民拒款风潮,民众纷纷购买全浙铁路公司股票。清政府却不顾浙人反对,1908年3月仍与英商签订了《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对内称为《沪杭甬铁路存款章程》),借款150万镑。浙江商民的抗争焦点随之从拒款转向保路。而为破坏浙路的修建,1909年间,朝廷也不断以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的任命,试图将汤寿潜调离浙江。1910年8月,更将汤革职,不准其再干预路事。浙江绅商因此成立浙路维持会,要求留汤办路,运动也日益深化。
以此反观贵林的行迹,其大致参加了浙江拒款保路运动的全过程,而且屡屡建言,态度相当积极。最初在1907年11月14日由浙江铁路学校发起召开的省城各校认股会上,关于“研究交款方法”一项,贵林不赞成“五年交清”,而倾向以十年为期,理由是:“付款期长,清苦学生亦可认股;倘限期过短,诸多不便。”[45]这是出于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而提出的合理建议,也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而在汤寿潜被革职后,贵林不但参加了1910年10月1日由全浙商务总会召集各分会分所“公谋维持办法”的大会,而且被一百多与会者公推为主席,主持了四条维持浙路方法的讨论与修订。其中最为关键的第三条,原拟为:“公同研究《公司律》进退商办总理权限,议决后,呈由抚宪分别奏咨。”经楼守光(醰安)、褚辅成(慧僧)提出:“今日之会由商会发生,当注重政府违背《商律》。似应联络全省,诘问商部。”“商会之设,责在保商。全浙实业仅此数百里之铁路稍有成效,而政府任情摧残,破坏《商律》,商人无所适从,商会形同虚设,竟可从此解散。现在惟有派员进京,要求商部尊重《商律·公司律》;要求无效,一律解散。”对此激烈主张,贵林也表示同意,并倡议“即日实行”,获得大众赞成,此条因此改为:“决派代表入都,呈请商部代奏,保存《商律》,俾达收回成命之目的。”其中所表达的指认政府革去汤寿潜浙铁公司总理之职为违法,从地方官代奏变为直接派代表进京,以示“持死力争”[46]的决心,凡此,抗议清廷的指向均极为显明。
就个人姿态而言,贵林的主张可谓相当激进。1910年9月9日召开的浙路维持会一开场,贵林即率先发言,提议:
此次政府咎汤,无端牵涉路事,破坏商办,违背先朝成宪,事关东南大局,危亡所系,凡属国民,万不能再安缄默。其办法应分为两团体:(一)为法定团体,如股东等应主和平;(二)为人民团体,不厌激烈。即日公电军机处、都察院、邮传部等声明:汤以言得罪,于路有功,力请代奏。颁布后命,解释谕旨界说,收回“不准干预路事”成命,以安东南人心。否则南洋劝业,招致华侨,亟亟提倡实业,概归无效。有血气者忿蹈东海,卑卑者竞隶外籍,朝鲜前车,庚子顺民,人心解体,国本大伤。
并在商讨最后办法“万一政府主持压力,人民呼吁概置不理,应再派人叩阍,并吁求台谏联合奏参,为再接再厉之举”时,“尤形忿激”,声言:“最后办法诸君即不赞成,鄙人必独行其是;即获严谴,为汤寿潜第二,或竟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记者称其“语语血诚,会众为之动容”[47],当系写实。
贵林所述尽管言辞激切,但若仔细体察,还是可以分辨出其维护朝廷或曰国家大局的良苦用心。所谓“不厌激烈”,并非走向革命一途,而是就表达的形式立说,因“最后办法”已将赴京请命设定为最高级别的抗争手段。身处地方,贵林其实早已如杭州将军瑞兴一般,切实感知到“人情愤激,官力难遏,大有横决暴动之势”[48]的统治危机。作为满人群体中的一员,又深受儒家忠孝观念熏陶,贵林此时只能期盼朝廷的改弦更张、顺从民意,以求消弭正在迅速积聚的革命情绪,是即“以安东南人心”之真意。故其“血诚”,实可自代表民意与为清廷着想两面言之。
参与拒款保路历次集会时,贵林多半被视为旗营的民意代表,不过,他所拥有的满营武官身份,仍潜在地发挥作用。如1907年12月2日全浙拒款会代表进见巡抚冯汝骙,“各代表排次入花厅”,而以“驻防贵翰香君居首”,以下顺序为留日代表、杭州等十一府代表、副会长王廷扬,“以次站立”等候。这一序列无疑凸显了贵林在众代表中的特殊地位。入座后,冯氏也先向贵林发问:“杭城女学堂有几所?”显然也对贵林的热心女学有所耳闻。而贵林亦率先将话头转向主题:“此次中丞到浙,百姓仰望久矣。浙路借款问题,全仗大公祖主持。”并称:“满营及各府近已集款至四千万余元,筑造全浙铁路,已绰绰有余,何待外债?”而对于拒款会的作用,也专从安定人心一面立说:“拒款会未设以前,省城人心恐慌,大有纷扰之势。自拒款会成立后,人心稍安。”[49]这自然也是贵林积极参与保路运动、希望能够控制局势发展的一个出发点。
不过,贵林亦官亦民、处处争先的角色,既为其在一系列社会活动中赢得了声望,也招致了诸多不满。譬如1907年9月22日,浙江教育总会开成立大会,贵林谋求成为代表杭州府的唯一一名临时干事,以便对会长的选举拥有更大发言权,当场即“致各府来会者大哗”,并遭温州二人大力指斥。[50]而关于1909年11月6日下午的会议报道,则被《申报》讥讽性地标题为《全浙教育总会尚武之气概》。所记会场中的煞尾动作,即贵林的发言,“归咎于从前会长(按:指项崧,温州瑞安人)之放弃,大发牢骚,骂詈多时,若以此尽到会之义务者然”,责备的语气已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一个月后保路会召开的挽留汤寿潜大会上,贵林的举动更是令人侧目。因“三时四十分钟入席,默坐许久,尚无人登台报告”,以来宾身份临场的贵林便跃身而出,演出了如下一幕:
来宾贵翰香突然登台诘问:“今日会事究系何人主持?似此推诿,实属不成事体。”复又盛气演说汤京卿必不就职,可以无庸发电挽留之原因,并痛骂浙江绅士之凉血;语次,忽又牵涉国民捐,谓拟发起,凡现办公益之人,月薪在三十元以上者,月捐二成,集款开设国民银行。方在手舞足蹈、兴高采烈之际,商会业董王湘泉君愤甚,不俟其辞毕,突然登台谓:“贵君所说问题重大,与今日开会宗旨渺不相涉,可请另日再议。”即照秩序,请会众推举临时主席。当推定陈介石主政,为临时议长。贵赧颜退席,意兴索然。[51]
若论贵林此次的越位发言,原本事出有因,但因其言辞过于得罪在场绅商,且表现欲太强烈,乃至反客为主、另设议题,不免被自认主人的商董抢白。而其对帮助政府偿还国债所举办的国民捐极为倾心,于此也尽显无遗。
然而,以贵林之说辞动听,无论官方主持还是民间社团的集会,仍然不时有会议主持人请其代为发言。如1908年12月19日,贵林受浙江农工商矿局总办、农工研究会监督汤汝和(字味梅)委任,“代表报告本会组织情形”;1909年11月6日,欢送汤寿潜大会临时主席陈黻宸又委托贵林“代表演说”等。[52]诸如此类的代言,当然也有益于提高贵林的社会知名度。
总体而言,贵林在清末浙江新政中不乏可圈可点的精彩表现,于办女学、争路权、偿国债方面尤其突出。其立场大体接近立宪党人,不过,与本地汉族绅商更关注保路不同,贵林是以同样的热情参与维护路权和发起国民捐。前者包含了地方利益与国家权益两个层面的内涵,其兴起及迅速扩大蔓延的趋势直接与朝廷的旨意相冲突,亦令地方官感觉棘手;后者则因其为国分忧的单一性,而得到了当地各级官员的普遍支持[53]。由此显示了贵林所持守的国家至上理念,以及在其意识中,朝廷与国家二者既可以分离[54],又具有相关性。分离是一种理性判断的结果,故对朝廷有不满以至抗议;合一则更多属于身为满人的情感认同,因而即使是最激烈的抗争,在贵林也是出于“爱国”的宗旨、“恨铁不成钢”的心意。此外,其不甘人后、能言善辩的突出个性,又引起不少人的反感。不排除贵林的争强好胜中有个人成名甚至揽权的成分,但其人之热心公益,即使厌恶、反对者也并不否认。毕竟性格问题是小节,政治诉求的相近为大义,以仗义执言姿态出现于公众场合的“旗营第一人才”[55]贵林,也因此在立宪党人中获得了更多的赞誉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