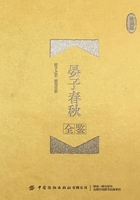
景公问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对以问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问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
晏子对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其处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诛不避贵,赏不遗贱;不淫于乐,不遁[1]于哀;尽智导民而不伐[2]焉,劳力事民而不责焉;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刑罚中于法,废置顺于民。是以贤者处上而不华,不肖者处下而不怨,四海之内,社稷[3]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厚利,死有遗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图。
晏子曰:“臣闻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今君税敛重,故民心离;市买悖,故商旅绝;玩好充,故家货殚[4]。积邪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嗜欲备于侧,毁非满于国,而公不图。”
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宫室不饰,业土不成,止役轻税,上下行之,而百姓相亲。
[1]遁:逃避。
[2]伐:此处用为自我夸耀之意。
[3]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因为古代君主都祭社稷,后来就用社稷指代国家。
[4]殚(dān):尽,用尽。
景公问晏子:“古代使国家昌盛的圣明之君,他们的德行怎样呢?”
晏子回答:“自身节俭而厚待百姓,对自身严格约束而对世人宽容;他们身居君上之位,足能以清明的政事施行教化百姓,而不以武力威迫天下;他们向民间征取财物,总是先去权衡有无,均衡贫富,而不以横征暴敛来满足自己的嗜好与欲望;诛罚犯罪之人时从不回避权贵,奖赏时不遗弃贫贱的民众;不过度淫逸作乐,也不沉溺于哀伤;竭尽自己的智慧引导人民,而从不因此自我夸耀,劳累身心勤于政事,而从不责备怨恨于民;治理国家政事崇尚相互有利,所以百姓不以谋取单方利益而去相互伤害;施行教化崇尚相互爱护,所以百姓不以相互怨恨为荣;制定的刑罚适中合乎法律,废除的法令罪名都能顺于民心。所以,贤德之人身处高位而不得意浮华,平庸之人身处低位而没有怨言,四海之内,社稷之中,全国民众,都能统一思想欲望,对待国家的政事就像是处理自家的家务一样。活着的时候对百姓施以厚利,死去的时候,能为民众遗留下良好的教化,这就是使国家昌盛的圣明之君的德行。”景公听完之后并不放在心上。
晏子接着说:“我听说,问道的人会更正自己的行为,听道的人会更新容貌。如今君王赋税征敛沉重,所以就会民心离散;市井之中的买卖双方违背常理相互冲突,所以商旅之人就会绝迹;君王玩乐的物品充裕,所以民间的生活用品竭尽。邪僻聚积于君上,那么蓄积的怨恨就会深藏于民心,所有的嗜好欲望都齐备在身边,馋毁诽谤之风充满了整个国家,而主公您却不放在心上。”
景公说:“好吧。”于是,下令一切玩乐的物品不再使用,公布市井之中的买卖不许相互欺诈,宫室不再装饰,高大的土木建筑也不再进行,停止劳役、减轻赋税,君上与臣下共同遵循行为规律去做事,从此以后,百姓也都能相互亲近,举国上下和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