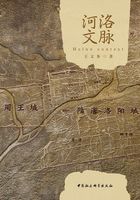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洛阳文学
概述
东汉在洛阳兴办太学,佛教传入,皇权重视文治,作好辞赋就可以当官等,为后世思想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权或割据鼎立,或南北对峙,动乱分裂,更迭迅速。灾难沉重的社会现实使人们不断在精神世界寻求拓展,精神生活空间变得异常自由开阔。
老庄思想起于河洛,作为儒学的重要对立面而存在。它主张遵从人的自然本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老庄思想标榜,根本内涵是对个性价值的重视,同时以玄学新形式流行于思想文化领域。洛阳郭象注《庄子》,强调物任其性,将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为士人身居庙堂而又追求心在山林的清高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玄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玄学对宇宙本体和各种事物名理以及人的才性进行辨析,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玄学清谈便针对有与无、言与意、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这种争论基本上在河洛区域内展开。从精神实质上围绕人的存在问题展开思考,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新的情趣体验人生的思想观念由此形成。宏大自我、崇尚内心自由成为新的人生目标,追求符合天性、富有才情的人格美为一时风尚。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迅猛的势头发展,影响波及的文化领域和阶层范围极其广泛。西晋时洛阳有佛寺几十所,北魏则多达上千所。闻名于世的少林寺、龙门石窟始建于这一时期。河洛出现不少名僧,文人信佛的不在少数。宗炳专程上庐山与名僧慧远研讨佛教经义。佛学逐渐融入中国思想文化长河,对我国哲学及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摆脱了天命神意的左右之后,人的才性、人的情感受到重视,那种把个人看成社会附属品的思想日益衰微,个体价值极度高扬,文学价值和文人地位不断提高。文人为了追求个体的不朽而从事创作,在文学上投入极大的创作热情,勇于追求美的创造,在题材开拓和艺术创新方面取得远超前人的巨大成就。
河洛文学在这样的文化潮流和社会趋势下,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文学创作领域呈现活跃状态。洛阳王都文化底蕴和山水人文景观赋予文人精神气质,河洛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既基于地理位置和文化积淀等方面因素,又脱离不了历史文化背景。
西晋至北魏,中国文学创作活动基本在河洛地区展开,全国各地大多数作家活跃于河洛一带。特别是建安时期,曹氏三父子均嗜好并提倡文学,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呈众星拱月之势。曹丕称帝后的活动主要在洛、许之间。河洛地区聚集了全国绝大多数作家,“三曹”“七子”,阮瑀、应玚、蔡琰、邯郸淳、繁钦、应璩等。西晋王朝建立,洛阳依然处于权力中枢位置,文学发展在全国占最大优势。称名于时的文人有潘岳、潘尼等。陆机、陆云由吴入洛,名动一时。“竹林七贤”活动于河洛,“金谷二十四友”齐聚洛阳,他们各具风采,争奇斗艳,使洛阳成了文学艺术荟萃之都,为河洛大地留下了无数瑰丽华章。虽然他们的很多作品并不是作于洛阳,但他们与洛阳有不解之缘,与洛阳关系密切的佳作也不在少数。如曹操的《蒿里行》和《薤露行》伤悼洛阳被毁;孔融成名于洛阳,活动于洛阳;曹植《送应氏》《赠白马王彪》两篇名作的产生与洛阳有关,《洛神赋》更是千古传诵。左思闭门宜春里,构思十年,杰作《三都赋》使洛阳纸贵;巩义潘岳挥笔叙哀情,风韵清丽,诗歌被《诗品》列入上品,辞赋在《文选》中数量居于首位,与陆机并称“潘陆”,并有“掷果盈车”美谈。陆机《洛阳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使古都洛阳的辉煌永载史册,也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灵感与题材。另外,从“乐不思蜀”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千古流传的洛阳典故、传说,也成为河洛文学长河中美丽的浪花。文明的发源地和建都城于洛阳等历史原因,河洛一带历来成为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很多家族中出过多位有名的文学家,传承博雅宏深的文化修养。同时洛阳作为一个都城景观意象,其内涵日益得到创造和丰富。
“八王之乱”,晋室南迁,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由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城。几乎所有文化根基深厚的世族大家都在永嘉之乱间,随王室相继流亡到南方。南迁文人在气候温和、风景秀美的江南繁衍生息,将博大深厚的河洛文化带到南国,河洛文学在此一脉相承,继续发展。吴越之地从此步入文学的全面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