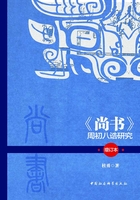
二 《洛诰》的错简问题
《洛浩》除篇末为史逸记事之辞外,通篇皆为周公与成王的对答之语,制诰者非周公即成王,灼然可见,因而不存在作者问题。但《洛诰》有缺文错简,却不可忽视。
《洛诰》有错简,苏轼以为《康诰》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至“乃洪大诰治”等四十八字即是《洛诰》之文。据《召诰》、《洛诰》可知,周公在三月乙卯朝至于洛,是月丙午朏,乙卯为十日,故“哉生魄”(初吉)应为“既生魄”之讹。召公于三月三日(戊申)至洛,正值哉生魄,盖史臣将召公至洛月相误移于周公。从《洛诰》行文来看,开篇即言“周公拜手稽首”云云,殊嫌突兀,以此四十八字移为序文,正与诰体相合。苏轼以此四十八字为《洛诰》错简,比后儒坚持置之《大诰》、《康诰》、《梓材》、《召诰》、《多士》显得要合理得多。
《洛诰》的错简,更严重的是郭沫若以为有《鲁诰》佚文的串入。郭氏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说:“其自‘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以下,直至‘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夙夜毖祀’一节,插在王与周公对话之间,与上下文了不相属。……余谓此等辞句均周公教导伯禽之语也。”又谓“王若曰”节为“成王诰命伯禽之文”,“当作周公告戒伯禽者之前”[13]。此即《鲁诰》窜入《洛诰》者。所谓《鲁诰》就是《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说的《伯禽》之命。郭氏此说可能受到郑玄的影响。郑玄注《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有云:“使史逸读所作册祝之书,告神以周公其宜立于后者。谓将封伯禽也。”[14]郑玄这一说法颇有望文生义之嫌。“王命周公后”在《洛诰》中凡三见,如果前引两条语义不明,下一条则把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蔡传云:“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后治洛。盖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迁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则未欲舍镐京而废祖宗之旧。故于洛邑举祀发政之后,即欲归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先儒谓封伯禽以为鲁后者,非是。”王国维《洛诰解》无疑对蔡沈的意见是首肯的,他说:“‘予小子其退’以下,则又成王将归宗周。命公留守新邑之辞也。后者,王先归宗周,命公留雒,则为后矣。……时虽行宗礼,四方尚有未服者,故命公留新邑以镇之也。”可见郑玄“立后”之说,实为曲解经文,不可信从。
郭沫若以为《洛诰》之中有《鲁诰》窜入,虽未称引郑说,实则异曲同工。郭氏不以郑说为据,大概是因为他有新的证据,这就是《令彝》“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之铭。郭氏以《令彝》证《洛诰》,认为“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之“明保”与《令彝》之“明保”同为人名,系指鲁公伯禽,因读此句为:“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与《康诰》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为例正同。[15]按郭说之有失偏颇是异常明显的。其一,《洛诰》中的“明保”绝非人名,当为勉保之意[16],不能与《令彝》中周公之子“明保”牵合为一。其二,就算是《洛诰》中的“明保”为伯禽,成王也不能以“予冲子”相呼。“予冲子”自称为“示谦”,称人则等于说“我的孩子”,伯禽与成王同辈,成王即使“示爱”也不应有如此称呼。其三,此所谓《鲁诰》半为成王之命,半为周公之言,何以一诰分由两人共作,且有对答之语?其四,周公教伯禽何来“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成王命伯禽何以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这恐怕没有什么特殊的道理可说。总之,视此节为《鲁诰》佚文,多有欠通之处。
黎子耀与郭氏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以下至“刑四方,其世享”一段诰词,原在《召诰》篇末,错在此篇,理由是《洛诰》和《令彝》中的“明保”非伯禽而是召公奭,又据此认为《召诰》乃召公封燕之诰。[17]黎氏与郭说商榷的结果,既承续其误,又别生葛藤,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在此就不多谈了。
我们不同意《洛诰》之中有《鲁诰》或《召诰》之文窜入,并不是说《洛诰》就无缺文错简,而是说对何处有“缺文”、何处是错简,当持谨慎态度。如果轻易将诰辞割裂开来,《洛诰》所记周公营洛与还政之本事遂沉霾不显,此于古史研究并无多大益处。宋金履祥《尚书表注》说:“《召诰》、《洛诰》相为首尾,惟《洛诰》所纪若无伦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图卜往复之辞,有周公归周迎王往洛对答之辞,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后而归之辞,有周公留洛相勉叙述之辞。辞从其辞,事从其事,各以类附,然无往来先后之叙,盖其年月必已具在系年之史,故此篇各以类附,不嫌其乱杂。但其间亦必有缺文错简。”金氏所言,大体不差,尤其是不以缺文错简而肆意割裂经文的做法,甚为可取。
以上通过对《洛诰》错简问题的检讨,说明所记并无大误,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其材料来进一步探索二诰的制作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