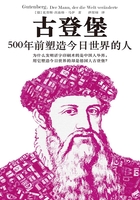
第二章 与人文主义的相遇
书籍的世界
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发明为新世界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这具体体现在印刷书籍和传单创造的新的信息沟通形式。在这之前,他必然要先接触书籍的世界,只有自己先接触了沟通发生地、沟通者和沟通媒介,才有可能认识到这种沟通形式也可以成为全新的、巨大的市场。大学集合了上述要素,那里有教授、学者、学生,还有图书馆。
与现在相比,当时的书籍更多的是纯粹的知识载体。大学学习让亨内认识蕴含在书籍中的世界。通过课本中丰富的插图和各种精美的手写字体,书籍带来的美学享受毋庸置疑。然而,大学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掌握知识,字体的艺术性再强,也只是知识内涵奢侈的外在形式,就像精美的圣骨匣为了圣骨而存在,是圣骨赋予了圣骨匣真正的价值。我们不应局限于今天对于知识的理解,在当时,知识更多地被理解为可定性而非可量化的。
1418年初,亨内·拉登沿着古贸易干道王者之路(Via Regia)[1],穿过布吕尔门(Brühler Tor)来到埃尔福特,此时的埃尔福特已不再像100年前时那样是德意志的第三大城市,但因为埃克哈特大师曾在这里的多明我会修道院为见习修士做著名的教诲演讲[32],埃尔福特仍可跻身帝国大都市的行列。亨内不会对这里感到陌生,因为与美因茨一样,埃尔福特的一切都充满商业气息。
亨内应该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充足的现金,以免因注册费、住宿费、书本费、服装费而捉襟见肘。由于亨内的堂兄弗里勒·拉登和鲁勒曼·拉登已经在埃尔福特开始学业,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得以提前了解关于费用的信息。
克雷默桥(Krämerbrücke)西侧的广场因旁边的教堂而被当时的埃尔福特人称为“圣本笃旁”(bei St. Benedicti)。从这里出发,有一条通往阿姆普罗尼亚纳(Amploniana)——其所在的宅院当时被称为“天堂之门”(Zur Himmelspforte)——的长长的街道。如果美因茨圣维克多教堂的教区主教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真的向亨内推荐了埃尔福特大学,那么后者毫无疑问会选择在这位主教捐赠和管辖的阿姆普罗尼亚纳生活和学习。
阿姆普罗尼亚纳此时已发展成了一处集学生和教师宿舍、图书馆、练习室、教室、经营场所于一体的校园。除了一些必备的神学书籍,图书馆还藏有医学和哲学书籍,此外还有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作品,包括彼特拉克的伦理学著作《幸运与不幸之药方》(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论僧侣的休闲》(De otio religiosorum)及其自传作品《孤独人生》(De vitasolitaria)。亨内还能读到乔瓦尼·薄伽丘的《论名人命运》(De casibus virorum illustrium),体会名人们曲折的人生,此外还有知名女性的传记合集《论名女人》(De mulieribus claris)。
图书馆中收录了众多当时常见的神学和哲学作品,例如彼得·伦巴德(Petrus Lombardus)的语录、埃吉狄乌斯·罗马努斯(緈gidius Romanus)的《定理》(Theorema)、波爱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 philosophiae)、亚里士多德的传世之作、米歇尔·斯科特斯(Michael Scotus)的《基督教信仰》(De arte fidei catholicae),此外还有诸多来自奥古斯丁(Augustinus)、圣维克托的雨果(Hugo von St. Viktor)、里拉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Lyra)、坎特伯雷的安塞尔姆(Anselm von Canterbury)、尊者比德(Beda Venerabilis)、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Bernhard von Clairvaux)、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让·热尔松(Jean Gerson)的作品,当然,这座图书馆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唯名论者奥卡姆的威廉的大作[33]。这里仅举几例,实际馆藏远不止如此。
与所有大学新生一样,亨内首先要完成基础的博雅教育,取得“自由七艺大师”(magister in artibus)的头衔,然后才能开始真正的专业学习,即神学、医学或法学。
埃尔福特大学由不同学系组成,而非民族团[2]。在进入神学系、医学系或法学系进行专业学习之前,学生必须先在人文系完成基础课程,成为自由七艺大师。
自由七艺可进一步划分为三艺和四艺(quadrivium)。三艺中除文法和修辞外还包括辩证,即论证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Organon)是辩证的基础,它为辩证提供了科学的工具。
中世纪时,人们用“哲学家”称呼亚里士多德,视其为哲学上的权威。来自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伊本·路西德(Ibn Ruschd)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研究大家,他的译介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拉丁语世界对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的认识。在拉丁语世界中,伊本·路西德也以其拉丁语化的名称“阿威罗伊”(Averroës)闻名,人们称他为“评论家”。
直到柏拉图思想复兴,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哲学才进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对此我们不进一步展开,但不容忽视的是以下事实:正是古登堡的印刷术让柏拉图作品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例如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将柏拉图作品翻译成了拉丁语,威尼斯的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以希腊语原文印刷出版了柏拉图作品。古登堡的创新是文艺复兴哲学、德意志人文主义以及宗教改革取得胜利的前提。
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查证亨内·拉登是否使用了阿姆普罗尼亚纳图书馆以及可能读了哪些书。或许不应对此产生过多幻想,因为学业本身——上课和练习——就已经占据许多时间,只有格外勤奋的学生才会在完成学习任务后继续在图书馆阅读。联系到亨内之后的人生道路,很难认为他对深入学习和对理论本身具有强烈的兴趣,与此相反,他之后展现出的是非常现实的头脑,正是这点带他走上了从商、建立企业的道路。
三艺之后要学习的是四艺,即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
只要对拉丁语有一定了解,基本上就满足了大学的入学条件。当时的孩子一般在十三四岁时注册入学,甚至还有12岁的大学生。如果亨内在17或18岁时到埃尔福特上大学,也在正常年龄范围之内。因为学生们中多数还都只是小男孩或者少年,有必要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严格管理和持续监督,这项任务由居住在学院的教师负责。
虽然内部管理严格,但官方的纪律规范几乎无法在这里得到落实。作为大学生的亨内不归城市司法机关管辖,而是由大学司法机关管辖。这在中世纪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当时对不同的人群设有不同的法庭:宗教界人士只能被宗教法庭传唤;与大学有关的人只能由大学法庭传唤;在美因茨,铸币会成员也有自己的法庭,就设立在铸币会楼里,由铸币会会长管辖,其他人没有权力对他们进行审判。
“脱落”(deposition)是埃尔福特大学新生开启大学生活的一种习俗。在这之前,亨内要向院长发誓,表示顺从。对于新生而言,“脱落”是一项花费不菲的仪式,同时也是怪异却又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人们丢给亨内一件罩衫,为他戴上一张既像驴又像猪的面具。高年级学生辱骂他,然后像洗礼一般反复往他身上浇冷水。水洗净了罩衫,也使面具慢慢变软。在软化溶解的面具下,他渐渐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在当时的学者眼中,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只是动物。相反,只有那些学习了三艺和四艺,甚至读了博士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人,才能称得上有文化。当时人们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项习俗,其基础似乎源于对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著名长篇小说《金驴记》(Der goldene Esel)流于表面的理解。在这个身体中甚至流动着贵族血液的城市贵族身上,除了城市贵族的骄傲,现在又加上了大学生的极度自信。
早上五点钟,亨内被叫醒。进行礼拜后,六点钟开始上课。他在十点钟吃第一餐。下午五点钟,晚餐摆上了食堂餐桌。两餐之间是他上讲座课的时间——教师不是自由地讲课,而是朗读书上的内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德语中“讲座课”(Vorlesung)这个词的本义是“朗读”。晚上八点钟,守卫锁上宿舍大门,但学生们知道哪里有通往夜生活的秘密通道,他们不仅知道,也亲身使用着这些通道。
对于亨内来说,找到进出校园的秘密通道完全可能比找到去图书馆的路更加容易。当时的埃尔福特并不是无趣的德意志小城市,而是一座大都市,就像一个世纪后的马丁·路德说的,整个城市是一个大酒店和大妓院。
当亨内·拉登在1418年初踏进这座属于美因茨选侯国的城市时,全新的篇章开始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新篇章,也是整个帝国甚至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新篇章。从1414年开始,基督教会在康斯坦茨召开大公会议[3],希望以此结束欧洲教会大分裂。教会几年前在比萨的第一次尝试不仅没有成功,实际上反而扩大了问题,因为对于1409年在那里选举出的教皇,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都不满意。在那次教皇选举之后,“可耻的双教皇”变成了“可憎的三教皇”。与此同时,欧洲的世俗统治者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教会权威的丧失也会动摇他们自己的权力。如果要避免自己被教会的失败波及,就必须结束这样的局面。
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自1411年起成为德意志的国王,他自认为是教会保护人并推行了多项倡议。强健的体魄让他得以多次考察整个欧洲,同各地当权者们共同商议,力求结束教会的分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人们想到的是使得早期基督教得以形成、相当于教会议会的大公会议。
大公会议成功的前提是,世俗领袖们和多数王侯支持这个大会并认可其产生的结果,国王的旅行外交对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不论是教士、主教、修会领导人,还是世俗王侯,都表示会将接下来的大公会议视为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普世的大公会议。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只有教皇有权召集大公会议,但三个教皇——罗马的格里高利十二世、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以及在比萨选出的约翰二十三世都不想冒被罢黜的风险。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他们通过拒绝行使召集权来阻止大公会议的召开。
西吉斯蒙德成功迫使约翰二十三世同意在康斯坦茨召开大公会议。1414年11月5日,大公会议开幕,在经历之前的不愉快之后,参会者重新坐在了一起,以求解决现存的问题。通过这次大公会议,基督的新代言人诞生了:无可挑剔的奥多·科隆纳(Oddo Colonna)。他来自历史悠久的罗马贵族家庭,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谦逊和虔诚为他赢得了好感。从此刻开始,阿维尼翁作为教皇所在地的日子永远地结束了。奥多·科隆纳为自己选了“马丁五世”这个称号,原因或许不只是他在1417年11月11日圣马丁节这天当选,而也是希望以此与特别崇尚圣马丁的法国人达成和解。
这次会议不仅重新统一了基督教,而且规定教皇必须定期召开大公会议。相较于基督代言人,大公会议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大公会议本来还应该成为修正和制衡教皇君主式强权的力量,这一作用因教皇们的阻挠而无法实现,但他们最终也为此付出了宗教改革的代价。
选出新教皇的消息传到了美因茨和埃尔特维勒,人们得知现在只有一个教皇了,没有人会再因选错教皇、选择成为教会分立论者而无法得到救赎,此时包括亨内在内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对教会而言,最大的罪孽是攻击教会的统一性,是分裂教会,而最歹毒的罪人便是造成和推动教会分裂的人,即教会分立论者;追随教会分立论者的人,意味着在末日审判时会跟他落得一样的下场,要跟他遭受同样的惩罚。
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也推动了帝国的改革和帝国管理的现代化,这对约翰内斯·古登堡本身及其印刷术的发明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次大公会议,古登堡是否还会发明活字印刷术?虽然从资料情况看,这是个纯推测性的问题,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可以做出“大概不会”的回答。西吉斯蒙德开始了帝国改革,之后腓特烈三世试图继续这项事业。在最开始时,这个大学生对此还一无所知,但几年后,他将对帝国改革进行认真的思考。
被合称为“胡斯战争”(Hussitenkriege)的一系列冲突很快发展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亨内虽然远在埃尔福特,但也觉得这些冲突似乎近在眼前。1415年,传道士、布拉格大学教授扬·胡斯(Jan Hus)在康斯坦茨被处以火刑。一年后,布拉格的杰罗姆(Hieronymus von Prag)也被处以火刑,他是胡斯的好友,曾向胡斯介绍了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思想。胡斯原本已经得到了国王关于其人身安全的承诺,却还是被判处火刑,这激起了拥护其宗教思想的捷克人的不满和反抗。埃尔福特神学家、奥斯定会成员约翰内斯·察哈里埃(Johannes Zachariae)在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与扬·胡斯展开论战。据说他证明了胡斯是异端,国王西吉斯蒙德因此赐予他“胡斯之鞭”(Hussomastrix)的尊称。在亨内到达埃尔福特的同时,西吉斯蒙德意志王授予约翰内斯·察哈里埃黄金美德玫瑰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身处埃尔福特的亨内·拉登在多个方面受到了布拉格系列事件的间接影响。埃尔福特大学的创始学者和最早的一批教授都来自布拉格。他们亲身经历了在那里发生的神学斗争。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本人也在布拉格上过大学。1418—1419年,亨内在埃尔福特大学就读时的校长是鲁道夫·迈斯特曼(Ludolph Meistermann),他曾就读于布拉格大学并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15世纪初,捷克人想加强自身在布拉格大学领导层的影响力,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而这首先体现在关于约翰·威克里夫的学说的争论上。
在这场大学教授之间的斗争以及关于威克里夫学说的争论中,迈斯特曼扮演了德意志教授代言人的角色,但他最终在与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Stanislaus von Znaim)和扬·胡斯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大主教布拉格的斯宾科(Zbynko von Prag)一开始支持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和扬·胡斯,但不久后就转而采取行动反对约翰·威克里夫的支持者。在这些斗争中,迈斯特曼受到了严重的攻击和伤害。德意志的教授们和学生们最终在1409年离开了布拉格。他们中的许多人去往刚成立了新大学的莱比锡,但也有一些来到了埃尔福特。一年之后,鲁道夫·迈斯特曼逐渐康复,他与布拉格大学校友海因里希·盖斯马尔(Heinrich Geismar)一样选择来到埃尔福特大学,成为人文系中重要且具影响力的一员。这场斗争在布拉格大学激起了轩然大波,其特别之处在于混合了民族目标、宗教观点和哲学基础。第一点对于亨内·拉登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埃尔福特与布拉格相距甚远;第二点最多对他稍有触及;但是第三点则对他产生了影响,这些哲学基础所塑造的认识方式和思考方式促使他做出了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决定,至少是潜在地影响了他。
想要探究最终使活字印刷术得以发明的基本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就应该了解当时的思想环境和大学课程内容。在对布拉格的威克里夫派之首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进行思想审判的文章中,在深入的神学讨论后,鲁道夫·迈斯特曼将话题引向了哲学基础。威克里夫派以唯实论为哲学基础,布拉格大学的德意志哲学家们则拒绝唯实论,称自己为唯名论者,他们排斥古代路线,追随现代路线。布拉格的德意志学者们将这种哲学带到了埃尔福特,旗帜鲜明地使唯名论成为埃尔福特大学的方法和世界观。
“布拉格人”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在“天堂之门”的规章中要求学生们使用唯名论的方法:“我希望他们认真努力地阅读,并在阅读时采用以下方法:就像现代人常做的那样,首先分析文章,从中得出结论……”[34]“现代人”(moderni)指的是唯名论者,他们追随的是现代路线。毫无疑问,亨内·拉登在学习自由七艺时使用的是现代路线的方法。他的课程中也包括以奥卡姆的威廉的方法为基础的逻辑学,其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唯名论的。
从根本上说,唯实论和唯名论争论的问题在于,人类、动物、植物、行星或恒星等普遍的概念(共相,universalien)是否有实体存在,抑或它们只是方便人们讨论和认识的概括实体或个体的名称,像数学公式一样不具备实体存在。
唯实论者认为共相属于实体,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共相是符号。近一个世纪后,唯名论成为正统思想,发展开始僵化,当时在埃尔福特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约多库斯·特鲁夫特(Jodokus Trutfetter)对唯名论提出了清晰而权威的定义:“共相是名称或者说法,但不是实体。”[35]这也正是亨内学到的内容。
阿姆普罗尼乌斯将唯实论者与胡斯派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扬·胡斯、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追随威克里夫的唯实论,鲁道夫·迈斯特曼也在控诉书中指出了这点。[36]亨内·拉登也是这样被告知的,在他必须牢记的学院守则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我也同样规定并命令,不准在课堂上公开或者私下里讨论拥护异教或胡斯派异端思想的材料,无论它是以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37]
在这个对异教徒和胡斯派思想提出警示并禁止教授相应内容的段落中,阿姆普罗尼乌斯还规定,为“真实存在的共相”辩护或者传播“关于真实事物多样性的观点”的学生将被当作异教徒开除,他坚决否定这两种思想。[38]对于唯名论者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而言,刚刚在康斯坦茨被处决的扬·胡斯和古代路线一样都是异端,在他看来,威克里夫和扬·胡斯的学说都以异端的唯名论为基础。古代路线直接通往地狱——亨内也是被这样教导的。
作为城市贵族家的儿子,亨内在成长过程中对城市贵族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以及维护其地位的决心耳濡目染,很早就开始面对日常的、最真实的现实世界。对亨内而言,奥卡姆的威廉的方法易于接受,因为后者的哲学将现实写进了理论,让理论拥有扎实的基础,不再虚无缥缈;他的哲学不是用抽象化和不停地创造定义来逃避实体,而是回归到了生活之中。
人们甚至可以在古登堡的实践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其构想和发明工作中看到威廉的三大原理。首先,奥卡姆的威廉要求不要将解释复杂化,要去除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这就是“奥卡姆的剃刀”。如果要思考一篇文章最简单的形式是什么,那么文章就被拆分成了词语,最后成了字母。其次,这位哲学家强烈推荐人们探寻认识的本源,探寻是从哪里了解到的某事,也就是说,不放过任何细节,再次从源头开始检验一切;对于古登堡的创新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发明家从源头开始进行新的思考和新的组合。最后,这位英格兰哲学家说:要保留组合,就要检验分离是否具有矛盾。
这三条原理都指向个体,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库尔特·弗拉施(Kurt Flasch)用下面这句话点明了威廉的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世界在形而上学的光辉中所失去的,思想在激进性上、行动在自由度上弥补了回来。”[39]对于奥卡姆的威廉来说,存在的只有单独的个体,而非普遍的共性。对于亨内·拉登而言,当他思考如何通过印刷来准确无误、完全相同地复制出尽可能多的文本时,作为字母载体的单个活字就成为个体。奥卡姆的哲学“准确地指出了是什么开始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中被广泛采纳——个体的优先地位”[40]。
埃尔福特大学所教授的正是这样的哲学,它增强了这位城市贵族子弟在自我负责行为、自由运营企业方面的观念。无独有偶,自由企业主曼斯菲尔德矿主汉斯·路德(Hans Luder)之子马丁·路德也有类似的经历,后者在一个世纪之后发掘了信仰中的个体地位,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登堡的发明,因为印刷术的发明为公开发表言论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威廉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点对亨内·拉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位英格兰哲学家看来,普遍的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只是符号,它们表达某物,概括实体存在,代表它们所表达之物。这些符号可以通过声音或者文字体现。符号的文字形式显示出,符号也是由更小的单元个体所组成的物质组合。因此,印刷不是复制文本,而是复制组成文本的字母。“奥卡姆认为概念是符号,而不再像以前的抽象理论那样认为概念是图像。”[41]
图像的复制在古登堡之前就已存在,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刻、上色并印刷。就像可以在木板上雕刻图片一样,也可以在木板上雕刻整张书页,但这意味着,要印刷一本100页的书就要雕刻100块木板。但如果从图像中抽离出来,将文本视为由符号组成的、可以互不矛盾地进行拆解的单元,那么将符号拆解为字母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一步。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亨内还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在最开始时或许通过金钱将他与字母联系到了一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