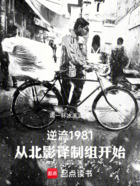
第29章 搞点宣传办法
《玉娇龙》的作者本名姓聂,曾用笔名金童,在《武林》、《浙江文艺》、《今古传奇》都有过工作经历。
《玉娇龙》这书也挺坎坷的,两三年后首次登载在《今古传奇》上,刚一刊载,就被上峰批判为“精神污染”。
今古编辑部当然也跟着连坐,差点没全面停刊。
当时编辑部里一位叫杨书案的老编辑与金童共同掌笔,将刚刊登的《玉娇龙》删改了十二万字,这才渡过难关。
提到《今古传奇》,就不得不提一人,就是杂志社的副主编罗维扬。
这人可以称之为八十年代文学界营销第一人。
罗副主编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给投稿来的小说改标题,而且是不经商量的擅自更改。
比如,曾经有一部名为《晚清名臣录》的小说投稿到今古编辑部,罗维扬看了,灵光一现,把这本书改名为《曾国藩密录》。
你还别说,效果奇佳,《今古传奇》的销量立即翻了三倍,作者看了内容才知道——哦,这是我的书啊。
金童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实则比李小霖大了十几岁。
他坐在许朝对面,一点看不出饱经沧桑的样子,要不怎么能在玉娇龙里写十几万字情色情节呢。
“这几天找你的人是不是挺多的?”
许朝对这位老编辑挺有好感,其实金童都算不上老编辑,比他资历年龄都大的还坚守在岗位上的老同志比比皆是。
金童为人谦和,头一回给许朝来信时也很有礼貌,完全没有老文学前辈的那股酸味与傲慢。
不是有句话吗?文字是了解另一个人的窗口,许朝和武林一直有通信,两人是初次见面,却像熟人似的。
有一词怎么说?书信频仍,晤面如故。
许朝给人倒了杯水,知道老金同志意有所指:“还成,我向厂里打了报告,暂时拒绝各家报纸的记者采访。”
金童正参观着许朝的宿舍,闻言回头看了他两眼,又笑:“这么好出名的机会,怎么反倒拒绝了?”
许朝也笑:“出名可未必是好事啊。”
“有觉悟,稿子存了多少了?”
“在那儿,您看看呗。”
金童拿起书桌边一叠稿纸,挺有厚度:“每天都写么?”
许朝吹着自个儿搪瓷杯里的热水,呼噜呼噜的:“写啊,写稿就得自律,写的久了养成习惯了,就觉得每天写那么多字也不过如此——您记得把稿费给我算上。”
“许朝同志,我发现你笔下的文字和你本人,差别还是很大的。”
“这话怎么说?”
金童分析道:“就拿你写的那个《一个待业青年的人生自述》举例,按理说能把一封信写的这么具有感染力,人生经验应该挺丰富,这种人的性格多半内敛、沉重,但你不一样,你是牙缝里插花,口齿很是热闹。”
许朝放了搪瓷杯:“我这算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话剧团的喜剧演员,台上再怎么高兴乐呵无厘头,台下有可能天生不爱笑;演雷雨的四凤,台上再怎么哀泣,生活里指不定是多开朗明媚的女同志。”
说到这里吗,许朝站起身来,双手抱臂:“老金同志,咱别贫嘴了,你就说吧,这趟从广州到京城来找我要提什么要求?”
老金刚要开口,许朝又补充了句:“咱先说好啊!虽然武林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就别开口了。”
这话听着像婉拒,其实不然,就好像过年给红包,小孩得三辞三让才能把红包拿着,一个道理。
老金同志还能听不出许朝的意思吗?
“你那篇《恩仇记》登载以后,咱社里销量翻了好几倍,编辑部的同志都很看重你,也很想见你的面,当面交流交流。
今年年底各杂志社、报刊都会聚在一起开个交流大会,牵头的是文协,你愿不愿意和我们《武林》一起去?”
就这事儿,金童需要特地往BJ跑一趟吗?这厮显然还在扔糖衣炮弹呢。
“去啊,去没问题,但我在文学界算哪根葱?要作品没作品,要知名度吧……今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老金同志,你们怎么不找找老一辈的文豪?”
金童摆了摆手:“这你就不用管了,只要你答应了就行。”
许朝预计这种交流会没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老一辈显摆资格,小一辈虚心受教,主流文学派占据主场,就和机关单位年会领导讲话似的,你就听吧!
不过就当见见世面也无妨,八十年代他还是有几个挺喜欢的作家的。
“这行,你继续说吧!”
“你在报纸上不是说,进了个剧组吗?好像还是拍武侠片的剧组,这可前所未有啊,武侠片之前可是禁区。”
许朝道:“这不是改开了嘛,金老先生不也从海峡对岸飞回来交流了一次。”
金童微微一笑:“我有个想法,你们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咱们武林能不能派出一两个记者同志一块儿进组,记录记录拍摄过程?”
嚯!这倒挺新鲜的。
其实许朝的第一反应是,金童想在《神秘的大佛》里植入广告。
显然这年头还没有商业片的模式,这就是后世看多了广告电影的不良反应。
不得不说,记录拍摄花絮这一招还行。
《武林》方面想给自己做宣传,一个是第一部武侠电影,一个又是武侠杂志,如果电影火了,宣传效果应该挺强。
毕竟各杂志报刊马上就要自负盈亏了,老金同志还是有几分真知灼见的。
“这我做不了主,我毕竟不是制作组的,就是个演员,定不了决策。但我能帮忙向导演反应,或者安排你们见一面,你看成不成?”
“成啊,当然成!”
金童喜不自胜,俩人又就《武林》近况聊了一回,老金同志忽然问了一句:“最近是不是从上海来的一位女编辑找过你?”
“有,说是《收获》的编辑,想问问我写不写严肃文学。”
“你答应了?”
“没呢,我写不来严肃文学。你认识她?”
“害,这谁能不认识,巴金先生的女儿,如今收获的副主编,要是不知道这位,可别说是在文坛混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