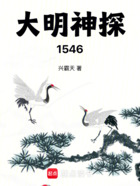
第1章 海氏兄弟
大明天下,有北直隶、南直隶、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俗称“两京一十三省”。
广东承宣布政使司,下辖十府及罗定直隶州一州。
十府中位于最南方的,是地处海南岛上的琼州府。
琼州府治,在琼山县。
这里于汉唐时属崖州,所谓天涯海角,孤悬海外,在中原人看来,实属荒蛮之地。
所幸如今已是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作为琼州府最为繁华的地方,琼山县的城景也像中原城镇一般,砖瓦建筑林立,街道宽敞,行人往来,商贩叫卖。
区别在于,中原小贩皆清一色的汉子,这里则多有女子身影,挑着担子,吆喝叫卖。
年轻的往往打扮得花枝招展,眼波流转,有的露腿赤足,落落大方,引得行人频频侧目。
只是这一日,大伙儿都顾不上看窈窕的小娘子了。
府衙差役捕手出动,手持棍棒清场,被驱赶到两侧的行人先是莫名其妙,待得护卫的人马自州衙而出,中央拱卫着一台大轿,招摇过市时,又忍不住议论开来。
“那轿子里坐的是谁?好大的排场!京师来的大官人么?”
“你竟不知?是安南国的王子出使啊!七日前就来了琼山,一直住在衙门里呢!他的手下每日出来采买,出手可大方了,都是要最好的!”
“安南……哦,交趾啊!”
大明永乐朝,曾将交趾收复,定为两京一十四省,后裁撤,交趾重新独立,对内称“大越”,对外称“安南”,以藩属自居。
对于安南国,广西和云南的百姓无疑更加熟悉,毕竟接壤,边境之地还有摩擦,但这里是广东海南,安南的商贾倒是偶尔坐船来此,可什么时候见过一国的使节?
“安南人入京朝贡,此后走我琼山北上么?”
“好事啊!这群安南人喜欢什么,赶明儿都卖它!”
瞧热闹的百姓交头接耳,察觉到商机的商贩兴高采烈,府衙官员骑在马上,与轿子并列,语气里则带着无奈:“黎正使莫要忘了自己的职责,还是回府衙吧!”
“小王本盼着尽早上京,奈何顾府尊不允,只让我耐心等待。承蒙诸位盛情款待,感激不尽,只是这府衙的日子,实在令人烦闷难耐……”
一道清朗的声音从轿子里传了出来,说的是大明官话,只是口音略显古怪:“年前偶得一部《新刊出像西游释厄传》,小王读后,叹为观止,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可惜只写到三十回,后续便无下文,听闻此书正是贵府才子所作,若能得见作者一面,实乃了却一桩心愿,还望邵推官成全,圆小王此愿!”
府衙官员皱起眉头:“我琼州书肆里多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青楼韵语》,琳琅满目,黎正使若是喜欢演义之作,大可随意阅览。”
安南王子失笑的声音从轿子里飘出:“不同!大不相同!小王独爱西游,烦请带路,见一见那位才子!”
“也罢,走吧!”
一行人浩浩荡荡,穿行街市,朝着西南而去。
琼山县终究不比江南大镇,半个时辰未到,一片青瓦高墙的建筑群便遥遥印入眼帘。
书声琅琅,墨香轻飘,颇有几分人文荟萃。
轿子落下,一位相貌儒雅,身材削瘦的男子从中走出,正是安南王子,府衙官员也下马,介绍道:“那便是东坡书院,琼山县学所在。”
安南王子打量着书院,由衷地道:“久仰了!”
府衙官员一奇:“黎正使早早听过这座书院?”
安南王子眼珠转了转,微笑反问:“《唐宋八大家文钞》里的东坡先生,小王岂能不知?”
“原来如此!”
府衙官员恍然,露出敬意:“四百多年前,花甲之年的东坡居士,三次受贬,至海南儋州,办学堂,兴学风……”
去岭南吃荔枝,是古代官员避之不及的噩梦,更别提直接贬到海南岛上,再下去就要去海里了,苏轼当年是真的挺惨,六十多岁的老人,还被这样折腾。
然而这位大文豪,却很豁达。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些诗词绝非牢骚与自嘲,苏轼到了儋州,不仅没有颓废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反倒大办学堂,吸引了许多文人一路远行追随,连带着整个海南的学风都盛行起来。
琼山与儋州同属海南,当年苏轼一叶孤舟,渡海而来之际,就曾借寓琼山的金粟庵,后来朝廷赦免,苏轼北返时,又于琼山暂住。
琼山本地人为纪念,便建了一座书院,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三十年前黎乱被毁,重新修葺,成了琼山县学,时人依旧习惯于称呼其作东坡书院。
安南王子聆听着,神色有些漫不经心,似乎对于过往的历史并不在意,等到介绍完毕,倒是迫不及待地道:“小王知晓了,我们去见一见那位编著西游的大才子吧!”
府衙官员有些不悦,侧头看向一下随行的师爷。
师爷心领神会,快步由侧门进入书院,先一步去寻人。
“请!”
府衙官员则领着安南使节一行,朝着书院走去,正巧教谕和训导匆匆迎出。
“啊?什么游?西什么?”
琼山县学的教谕是一位胡子花白的老者,慢吞吞的,口齿不清,好半晌才弄明白说的是啥,神色顿时变得愤慨:“取经的故事啊!那是海十三郎编的!唔!编到一半没了,气煞老夫!”
安南王子顿时感同身受起来,连连点头:“对对!唐僧赶走悟空后,在宝象国被那魔王所害,变作老虎,八戒到底有没有把大师兄寻回?唐僧是不是后悔错怪了这个徒儿?后续到底如何?”
“你没听老夫说么?后面没有啦!”
“哎呀!怎么能没有呢!”
眼见两人说着说着,竟都急了,府衙官员有些茫然。
不就是一部西游么?自宋元传下的剧目,让玄奘取经的故事变得家喻户晓,甚至收录进了《永乐大典》之中,此后各种新编也是层出不穷,怎么一个个多稀奇似的……
府衙官员没有看过那部前一阵传得挺火的新编西游,但在心里断定,不会是什么好作品,十之八九就与书肆里面卖的《精忠录》一样,将关于岳武穆的史书材料,拿白话讲一遍,把相关的奏章、题记、檄文、书信一股脑编进去,毫无文学性可言。
可如此差的质量,偏偏演义的销量惊人,甚至有一版专供内府,实在没道理,只能说演义之作,确实让不少人津津乐道。
安南蛮夷之地,不知经史子集乃学子首重,可现在县学老教谕竟也这般失态,让他难以理解。
所幸就在这时,先前派出去的师爷匆匆而归,来到身侧低声禀告:“东翁,著作者姓海名玥,尚未及冠,族中排行十三,在书院里被称作海十三郎。”
“还未及冠?”
如此年纪就能著书,哪怕是演义之作,倒也令人有些刮目相看,府衙官员免不了生出惋惜:“年少早慧,不求圣贤之道,却误入歧途……唉!”
师爷顿了顿,又接着道:“我见到了海十三郎,说及外藩使臣喜爱他新编的西游,他却无喜悦,反倒皱起眉头,有言不再分心他途,只求专心攻读,考取功名,以光耀门楣。”
“哦?”
府衙官员有些不信。
师爷补充道:“这位海十三郎还有一位同岁的兄弟,姓海名瑞,行次十四,被书院同窗称作‘道学先生’,便是当成先生来请教学问,都说是能成廪生的,两人便在一起备考,准备下月的县试。”
“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府衙官员颔首称赞,专于科考,亡羊补牢,这就挽回了不少印象分,再结合姓氏,喃喃低语:“应是故御史海澄的族人了!”
明朝海南有三位进士——李珊、海澄和陈实,分别当过南京监察御史、四川道监察御史和广西道监察御史,朝廷曾在他们的家乡,立了三座绣衣坊,其中海澄正是琼山海氏人,当地也尊称这一族为绣衣海氏。
这个姓氏不多见,家学渊源,应该没错。
这边低声讨论着学子的来历,那边安南王子和书院教谕也就西游交流好意见,朝着学堂走去。
书院内的学子早被惊动,听得是府衙来人,更有外藩使臣陪同,赶忙涌到门口,齐齐行大礼。
没有从众的,是坐在后排靠窗的两名学子。
一位身着月白澜衫,眉眼俊逸,身材高大,既有文人的清俊气质,又有其他学子不具备的雄俊魁伟,端的是仪表堂堂。
另一位五官与之稍有几分相似,穿着一袭浆洗得有些褪色的青衫,身材瘦长,骨骼锋棱,气宇间亦有股清硬不折之气。
“海玥!海瑞!”
众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越过前排,望向那不卑不亢的两位少年郎,生出赞叹:“绣衣海氏,好一对贤昆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