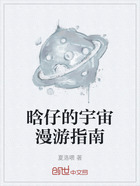
第9章 反物质:宇宙的银翼杀手
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就像屋檐下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你看,物理学的定律必须用数学公式来表达,比如人人都知道的E=mc²。物理问题也要靠数学计算解决,比如计算彗星多少年绕地球一圈——这就好比英语是莎士比亚的笔尖,而数学就是物理学的发声器官。
说实话,要是不懂数学的话,看物理学论文简直像读天书。可偏偏有些人,明明连三角函数都不会算,却天天喊着“推翻相对论“、“改写热力学定律“。知道我们怎么称呼这种人吗?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
反过来看,物理学也像数学的伯乐。要是没有物理需求,虚数这种抽象概念可能永远躺在数学课本里睡大觉。弦理论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物理学的候选终极理论,硬生生给数学界开辟了新的战场。
有时候直觉反而会蒙住我们的眼睛。比如量子粒子能穿透障碍物这种事,正常人都会觉得荒唐。可当数学公式明明白白算出来了,我们只能乖乖承认:“数字不会骗人。“这时候数学就像黑暗里的手电筒,带着我们穿过认知迷雾。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就像抛物线轨迹的计算,数学明明能算出无数种可能,但现实中要考虑空气阻力、风速这些物理限制。这时候数学就像任性的孩子,需要物理学拽着它的衣领说:“别异想天开了!“
这时候就看出数学和物理的微妙关系了。咱们来算这个抛物线方程:y=ax²+bx+c,当你解这个二次方程时,总会得到两个答案。就像你问手机导航“去车站怎么走“,它可能同时告诉你“往东走200米“和“往西游过太平洋“——数学可不管现实能不能实现。
这两个解里,总有个看着正常的:告诉你该用多大初速度发射物体。但另一个解就魔幻了,它会建议你“用负速度把炮弹砸进地里“。这时候物理学家会直接划掉这个解,毕竟现实世界有现实世界的规矩——炮弹穿不过水泥地,就像人不能在水面上走路。
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反而暴露了数学和物理的互补性。数学就像个开挂玩家,能算出所有可能性;而物理学家要当裁判,把违反物理定律的方案红牌罚下。这种看似矛盾的合作,在科学史上可是立过大功的。
你猜怎么着?正是这种“数学算出来但物理不认账“的情况,后来居然帮人类发现了反物质!当年物理学家们对着复数解头疼的时候,有个叫狄拉克的聪明人突然拍大腿:“谁说这些解没意义?它们说不定对应着镜像世界的粒子呢!“
这个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在纸上写下的一串复数解,怎么就掀开了反物质世界的帷幕?咱们得从头说起——那时候量子力学刚起步,科学家们连电子怎么运动都搞不清楚。狄拉克硬是盯着数学方程里那些“不现实“的解,发现了通往新世界的钥匙...
但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才刚开始。狄拉克像玩拼图似的,把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两块看似不搭的数学碎片硬生生拼在一起。要知道当时物理学家们有个心病:薛定谔方程处理不了接近光速的电子,就像普通计算器算不了微积分。
1928年某个深夜,狄拉克的钢笔突然在草稿纸上顿住了。他发现自己推导出的方程有个诡异特性——这个完美对称的数学式子里,电子居然可以带着正电荷跳舞!这好比煮饭时发现锅里凭空多出个倒着走的时钟,完全违背常识。
当时的物理学界炸锅了。诺奖得主玻尔当面嘲笑:“老兄,你这方程怕不是算出了镜中花水中月?“连爱因斯坦都挠头:“数学美得惊心动魄,可现实世界哪来的正电子?“但狄拉克梗着脖子坚持:“数学不会说谎,这些解就像海市蜃楼,肯定对应着真实存在的东西。“
命运总是眷顾倔脾气。1932年,安德森在云室实验中真的捕捉到了正电子的轨迹。那个本该被物理学家们扔进废纸篓的“错误解“,居然在现实世界找到了镜像。更绝的是,当物质与反物质相遇时,它们会像宿敌般同归于尽,化作绚丽的能量闪光——这恰好完美对应狄拉克方程里的湮灭项。
现在回头看,狄拉克方程就像把打开平行世界的钥匙。那些曾被视作“数学垃圾“的解,竟预言了整个反物质宇宙的存在。如今医院里的PET扫描仪能捕捉癌症,靠的正是正电子与人体组织湮灭时释放的伽马射线。谁说数学只是纸上谈兵?它分明是穿越现实与虚幻的任意门。
这时候整个物理学界就像被扔了颗深水炸弹。狄拉克的方程不仅预言了反电子,更捅破了“物质独大“的认知天花板。想象下你突然被告知:每个硬币都有正反面,但之前全人类都只见过硬币的正面——这就是当时科学家们受到的冲击。
实验室里的情景特别戏剧化。每当高能粒子对撞时,监测屏上总会闪现成对出现的粒子-反粒子,就像魔术师凭空变出双生玫瑰。最绝的是在日内瓦的CERN,科学家们造出的反质子能在磁场里跳恰恰舞——和普通质子旋转方向完全相反,活像照镜子。
但反物质有个致命弱点:它们和正常物质相遇时,会像宿敌般同归于尽。这个特性被科幻作家玩坏了,《天使与魔鬼》里那个能炸毁梵蒂冈的反物质炸弹,原型就来自这里。现实中,CERN每年造的反物质总量,还不够点亮一只萤火虫的尾巴。
最让人拍案的是宇宙射线中的发现。当来自深空的质子雨砸向大气层时,会炸出反μ子这种“异端粒子“。这些太空来客像幽灵般转瞬即逝,却在云室中留下清晰的双螺旋轨迹,仿佛宇宙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狄拉克这个数学预言最狠的地方在于,它捅破了物理学家最后的傲慢。以前总有人说“现实必须符合常识“,现在不得不承认:“常识不过是尚未被数学证伪的偏见。“就像当年哥白尼把地球踢出宇宙中心,狄拉克用方程证明了物质并非世界的唯一主角。
这就像宇宙给我们上演的终极魔术:物质与反物质这对双生子只要碰面,就会瞬间化作能量烟花。你钱包里的硬币要是正反面相撞,恐怕只会叮当响,但在粒子世界里,这样的相遇意味着惊天动地的能量释放——1克反物质湮灭产生的能量,足够把巴黎铁塔送上平流层。
现在让我们拆解这个魔术的机关。当电子遇上正电子,这对“量子怨侣“的湮灭过程堪称完美:他们的质量完全转化为两束背道而驰的γ射线光子,整个过程严格遵守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在日内瓦的CERN环形隧道里,科学家们就像量子红娘,专门撮合这些粒子对撞——只不过每次约会的结局都是壮烈的能量爆发。
更有趣的是粒子家族的“套娃式“存在。电子、缪子、陶子这三个轻子兄弟,质量分别是0.5MeV、105MeV、1777MeV,就像俄罗斯套娃般层层嵌套。而每个粒子还自带镜像反物质版本,再加上超对称理论预言的“超粒子“——这简直像在量子世界里开了家3D打印店,每个基础模型都能衍生出多个豪华版。
但最吊诡的谜题依然未解:为何我们宇宙中的物质比反物质多出十亿分之一?这个微小的不对称性,就像造物主在创世时手抖撒多了星尘。2020年日本超级神冈探测器发现中微子振荡中的CP破坏现象,或许正暗藏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想象一下,如果138亿年前正反物质完全对称湮灭,现在的宇宙恐怕只剩冰冷的光子之海。
反物质的应用早已走出科幻。医院里的PET扫描仪,正是利用正电子与人体组织湮灭产生的γ射线,绘制出癌细胞的热点图。而科幻作家津津乐道的反物质引擎,在理论上确实可行——1毫克反物质燃料就能让汽车绕地球三圈。只是目前人类制造反物质的效率,还赶不上蚂蚁搬运糖粒的速度。
狄拉克当年在方程里瞥见的镜像世界,如今已成为粒子物理学的基石。那些曾被视作数学冗余的解,不仅预言了反物质,更暗示着宇宙深层的对称密码。就像梵高画作中旋转的星空,微观世界的粒子之舞同样充满令人战栗的数学之美。
这个湮灭过程就像量子世界的“冰融为水“,只不过融化时迸发的是堪比超新星的能量。想象两个用特殊冰块雕成的天使雕像——当它们指尖相触的瞬间,不仅自身化为无形,还爆发出足以照亮整个展厅的炽热光芒。但量子世界的天使们更任性,它们必须严格按照物理定律来表演这场魔术。
在微观尺度上,粒子其实是能量场的特定振动模式。电子和正电子相遇时,就如同两股相反的涟漪在水面相遇。当它们的量子波函数完美重叠,电磁场的振动模式突然被改写,原本稳定的“驻波“形态瓦解,转化为传播形态的光波——这就是我们观测到的γ光子。
但整个过程充满量子世界的狡黠。这两个粒子并非像台球碰撞那样直接接触,而是通过交换虚光子来谈判“自杀协议“。它们会在相遇前进行无数次量子试探,就像两个特工在黑暗中用手电筒闪烁摩斯密码,直到找到彼此湮灭的完美时机和角度。
更神奇的是湮灭产物的随机性。虽然多数情况下产生两个背对背飞行的γ光子(遵守动量守恒),但在极端高能环境下,可能会诞生μ子对甚至顶夸克-反顶夸克对。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里,每秒钟都在上演这种量子俄罗斯轮盘赌——当质子与反质子以0.999999991倍光速对撞时,迸发的能量足够在飞秒级时间内重塑早期宇宙的炽热汤境。
反物质武器的构想虽震撼,实则受困于量子囚徒困境。要储存1克反物质,需要建造比地球磁场强百万倍的磁瓶,且容器的每个原子都需完美排列——任何细微扰动都会引发提前湮灭。这就像试图用蛛丝网兜住液态阳光,理论上可能,实操中近乎荒诞。
而最深刻的启示藏在湮灭过程的对称性中:物质与反物质的每次相遇,都在重演宇宙创生时的对称破缺。当我们看着PET扫描仪中正电子湮灭产生的γ射线时,其实是在观测138亿年前那场决定物质统治的量子天平倾斜的微型重演。每个湮灭事件,都是创世余晖的量子全息碎片
人们让普通粒子相撞就能造出新粒子。其实所有粒子碰撞的本质,都是旧粒子消失、新粒子诞生。那问题来了:当粒子和它的反粒子——这两个电荷相反的镜像存在——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首先它们会像磁铁般互相吸引,毕竟正负电荷天生就会凑到一块儿。更关键的是,它们的属性完全互补,一碰上就会彻底湮灭变成中性粒子,比如不带电的光子。不过这里有个重要前提:碰撞时必须遵守守恒法则。就像我们早就发现的,电荷绝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碰撞前后总电荷数永远相等。但说实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只是实验结果逼着我们承认这个规律。
举个具体例子:当电子遇到正电子这对反粒子时,它们会像久别重逢的恋人般急速靠近。正负电荷瞬间抵消,两个粒子化作光子消散在虚空里。但如果是两个普通电子相遇,它们的负电荷会像闹别扭的孩子互相推搡。即便强行把它们按在一起,最终也只能得到双倍负电荷,这时候连光子都懒得现身。
你可能以为只要电荷相反的粒子就能随便湮灭?比如拿带-1电荷的电子和带+1电荷的反缪子配对。结果实验告诉我们:没门!宇宙还有隐藏规则——每种粒子的“身份标签“(比如电子性、缪子性)也必须守恒,就像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不能随便丢弃。
想摧毁电子只能派出它的专属对手——正电子,用其他反粒子根本没用。就像你没法用灭鼠药消灭蟑螂,每种粒子都有自己的“天敌名单“。电子、缪子、陶子都有自己的反物质分身,必须严格配对才能触发湮灭。
更夸张的是,宇宙还藏着无数隐藏规则。比如组成质子的夸克必须三个一组打包出现,碰撞时不能单独拆卖——这被我们戏称为“三夸克铁律“。把这些零零碎碎的规则拼起来才明白:只有正反粒子这对死对头相遇时,才能上演同归于尽的戏码。
至于宇宙为什么制定这些奇葩规则?说实话,我们依然摸不透宇宙的脾气。或许某天会发现这些法则不过是更底层规律的副产品,但现在看来,反粒子就是破解宇宙密码的关键钥匙。
更有趣的是,反物质也能玩“拼积木“游戏。拿三个反夸克当积木块,能拼出反中子——这家伙外表和普通中子一样中性,但内部全由反物质构成。反质子就更带劲了,除了顶着负电荷这点不同,它简直就是穿了黑色西装的质子。
最疯狂的当属反原子:正电子绕着反质子转,完全复刻正常原子的结构,就像镜中世界的倒影。这些反物质造物遵循同样的物理法则,只不过浑身带“负能量“——只要和正常物质碰个指尖,瞬间就会炸成光子烟花。这种对称到极致又危险至极的特性,让反物质成为物理学家又爱又怕的“完美情人“。
把正电子绕反质子旋转的瞬间,你就解锁了反氢原子这件“镜面艺术品“。沿着这个思路疯狂堆料——用两个反氢搭一个反氧,就能造出反水分子。这瓶“镜像矿泉水“看似平平无奇,但只要你敢喝,体内的正常水分子就会和它上演湮灭烟花秀,释放的能量足够把整个街区炸上天。
这种疯狂玩法能无限套娃:反碳搭建反蛋白质骨架,反核苷酸编织反DNA双螺旋,甚至可能孕育出反细胞生命。细思极恐的是,或许在某个平行宇宙,反物质地球正上演着《镜像人生》——那里的反物质你正开着反汽油驱动的反汽车,用反硅基芯片的反手机收听这个节目。说不定那个世界的科学家也在苦恼:“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全是反物质?“
但这里藏着绝妙的讽刺:物质与反物质本质上是平等的镜面双生子。如果我们生存在反物质世界,照镜子时看到的“正常物质“反而会被贴上“反“标签。就像北半球的人总觉得南半球居民倒着走路,其实只是观察视角不同而已。
不过幻想再美也要面对残酷现实——放眼整个可观测宇宙,反物质就像集体玩失踪。虽说实验室里能造出反氢原子,但想存住它们比困住阳光还难,需要超导磁场的“光子牢笼“关押这些随时想自爆的囚徒。更诡异的是,当物理学家用精密仪器测量反物质的光谱特性,发现它们连发光频率都和正常物质严丝合缝,就像被设定好的镜像程序。
至于反物质有没有味道?理论上反咖啡应该和正常咖啡同样苦涩,但谁敢用舌头验证呢?或许某天我们能在绝对真空环境造出反巧克力,看着它与正常巧克力接触时炸出的伽马射线烟花,在毁灭中完成最浪漫的味觉实验。这些疯狂的想象不断提醒我们:宇宙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藏着远比小说更离奇的剧本。
反粒子和粒子在引力作用下会有相同还是相反的表现呢?更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周围全是普通物质而几乎找不到反物质?根据实际观测结果,普通物质几乎占据整个宇宙,反物质却像消失了一样。这说明宇宙中的物质总量绝对碾压反物质。如果按照物质与反物质完全对称的理论,宇宙大爆炸应该诞生等量的粒子与反粒子。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如果每个粒子都有对应的反粒子,最终所有粒子都会找到“另一半“完成湮灭,整个宇宙只会剩下光子在游荡。但现实狠狠打了这个假设的脸,毕竟我们身边除了光还有行星、恒星和人类。这意味着大爆炸时必定存在某种机制,使得物质产量远超反物质。
目前科学界有两种主流猜想,我试着用大白话讲清楚。第一种假说认为:大爆炸初期物质比反物质多出极其微小的数量,虽然绝大部分正反物质都湮灭成能量了,但多出来的那丁点物质残留下来,逐渐形成了星系、恒星,甚至暗物质(注意!这里要划重点——暗物质和反物质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种解释虽然能自圆其说,但聪明如你肯定发现了破绽——科学家只是把问题从“为何现在物质多“偷换成“为何最初物质多“,根本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那再说说第二种可能性:宇宙大爆炸时明明诞生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但某些粒子自带“作弊程序“,让物质逐渐占了上风。比如说,如果反物质像雪糕融化得比普通物质快,或者生成物质的生产线效率更高,哪怕两者差距只有亿分之一,经过138亿年漫长积累,最后也会形成压倒性优势。
这种说法看似巧妙,但有个致命漏洞——物理学定律向来讲究对称美。就像照镜子时,正反粒子应该遵循相同的物理规律。比如中子衰变成质子+电子+反中微子,反中子就应该完美对应地变成反质子+反电子+中微子,整个过程应该像照镜子般对称。但科学家们翻遍了粒子对撞机的数据,发现某些粒子在变身过程中确实存在0.0000001%的“偏心“,就像有人偷偷给物质加了根隐形的杠杆。
更气人的是,就算把这些实验发现的所有不平衡现象加起来,也只能解释现有物质总量的千分之一。就像你发现家里少了十斤大米,结果只在老鼠洞里找到一粒米,剩下的九斤九两依然下落不明。这逼得物理学家不得不承认:要么还存在某种未被发现的“物质作弊器“,要么整个理论框架需要推倒重来。
至于“宇宙分区域存在反物质“的脑洞?现实情况是,如果真存在反物质星系,星系交界处早该上演正反物质湮灭大戏,爆发出肉眼可见的伽马射线烟花。但人类架在天上的望远镜看了几十年,连个火星儿都没逮到。所以要么反物质文明都躲在138亿光年之外,要么这个猜想就和“地球是平的“属于同个级别的幻想。
接着这个思路往下推:既然整个银河系都找不到反物质天体,事情就变得更有趣了。想象一下,如果某个星云是反物质构成的,当星际尘埃飘过时,就会像在太空里点燃巨型镁条,爆发出511千电子伏特的伽马射线闪光——这种能量特征就像反物质的“死亡尖叫“。但现实是,费米伽马射线望远镜盯着银河系看了十几年,连个像样的“尖叫“都没捕捉到。
更绝的是,连宇宙射线都在作证。当高能质子从深空飞来时,如果途中有反物质区域拦截,它们的湮灭产物会像夜空中的闪光弹般醒目。但实际检测到的宇宙射线中,反质子含量不足百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刚好可以用普通宇宙射线碰撞来解释,根本不需要动用“反物质仓库“的理论。
不过最扎心的证据来自氢原子。星际空间飘荡的中性氢云,如果遇到反物质星际风,会像黄油碰热刀般瞬间湮灭。但天文学家通过21厘米谱线观测发现,从银河系这头到那头,中性氢都安安分分地存在着,连个缺口都没被啃出来。这种“宇宙级安宁“彻底堵死了“银河系存在反物质特区“的幻想。
所以现在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别说太阳系,整个银河系乃至本星系团,都是物质的绝对领地。那些关于“反物质宇宙“的科幻设定,要想符合现实物理规律,恐怕得把故事背景设在离我们至少数亿光年外的超星系团边缘——远到连湮灭产生的伽马射线都还没抵达地球。
接着咱们来戳破另一个迷思:如果整个星系都由反物质构成会怎样?想象两个星系像油滴和水滴般在宇宙中漂浮,交界处会迸发出持续数亿年的湮灭烟花,这种伽马射线暴的亮度足以照亮半个可观测宇宙。但现实是,费米望远镜连这种宇宙级“闪光弹“的残影都没捕捉到——整个室女座超星系团就像被宇宙安检员扫描过,连一粒反物质尘埃都藏不住。
说到中性粒子的反转版本,这里藏着更烧脑的设定。比如光子,这个传递电磁力的信使,科学家们玩了个文字游戏说“光子就是自己的反粒子“。但仔细想想,这就像说照镜子时镜中人就是你本人,完全回避了正反对立的本质。真正的中性粒子反物质之谜在中微子身上达到高潮——这些幽灵粒子如果被证实是马约拉纳粒子(自己能当自己的反物质),现有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就得重写三分之一。
最颠覆认知的是希格斯玻色子,这个赋予万物质量的“上帝粒子“,如果它也有反粒子,理论上应该和自己完全镜像对称。但大型强子对撞机撞出的数据就像量子骰子,至今没给出明确答案。这种不确定性让物理学家们夜不能寐,毕竟只要存在任何一个没有反粒子的例外,整个宇宙物质优势的源头就可能藏在这里。
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暗物质领域,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果暗物质粒子恰好是自身的反粒子,那它们可能在宇宙诞生初期就通过自我湮灭塑造了星系结构。这种猜想让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们疯狂调整对撞机参数,试图在亚原子碎屑中找到蛛丝马迹。但现实就像量子叠加态,所有可能性都同时存在,直到我们观测的那一刻才会坍缩成某个令人失望的结果。
这就像说你的好朋友就是你自己,那是不是等于没有朋友?同样的道理,波色子和交子这对小伙伴也遵循这个规律。
你可能发现了,这些传递作用力的粒子有个特点:带电的W粒子虽然也传递力,但它偏偏自带反粒子。这就引出个问题——为啥有些粒子有反物质分身,有些却没有?说实话我们也没完全搞懂,目前只知道带电粒子肯定有反粒子。其实说白了,这都是因为狄拉克方程里恰好存在复数解。
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觉得不带电的中微子可能也有反粒子。虽然它本身不带电荷,但在弱核力作用中会表现出某种“超赫电荷“的相反属性。不过中微子本身就神神秘秘的,我们节目里也说过,这种小东西特别难捕捉,研究起来像在迷雾里找萤火虫。搞不好中微子自己就是自己的反物质版本呢!不过说来说去,这些推测就像用谜语解释谜语。
那我们要怎么研究反物质呢?最直接的法子就是用反粒子拼装反物质。这主意听着就带劲对吧?不仅能满足好奇心,还能搞清楚反物质为啥存在,以及它和普通物质到底有啥不同。可惜实际操作比登天还难,光是摆弄普通粒子就够头疼了。你想想,要做块巧克力蛋糕得用上1后面跟着25个零那么多的质子!更别说反物质随时会和正常物质“同归于尽“——只要碰一下就会瞬间湮灭。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在实验室里让反质子和反电子和平共处,成功造出了反氢原子。
2010年那次实验确实很厉害——科学家不仅造出了几百个反氢原子,还把它们关在“笼子“里整整20分钟。但说实话,这就好比给你十粒芝麻让你研究芝麻饼的做法,根本尝不出个所以然。我们现在每年在实验室里造的反物质,少得需要用“皮克“这种比尘埃还小的单位来计算。要是想把这点反物质攒成葡萄干大小,估计得让人类文明再活个几百万年才行!
就算真攒够了,还有个更头疼的事——怎么保存这些“危险品“?总不能拿玻璃罐子装吧?科学家们想着用电磁场做成看不见的笼子,但这也只是纸上谈兵。现在咱们对反物质的认识,就像刚学会拼写自己名字的小孩:知道它真实存在,带相反电荷,和普通物质碰面会炸成烟花。可要问起“为什么宇宙偏爱普通物质“、“反物质会不会往下掉“这些关键问题,我们连答题纸都还没拿到。
说到重力效应就更有意思了:理论上反物质应该和普通物质一样受重力影响,但我们现在收集到的反物质样本,比沙漏里的沙子流得还快,根本来不及做实验验证。这就像明明知道派对上有神秘嘉宾,却只能隔着门缝听见脚步声。说到底,反物质之谜不仅是科学难题,更像是宇宙给我们出的终极谜语,而我们现在连谜面都没读全呢!
重力这家伙虽然天天把我们按在地面上,但论力气可是四大基本力里最虚的。您想啊,要测出苹果落地的力量都得搬座山那么多的粒子才行。反物质就更难伺候了——本来产量就比熊猫血还稀缺,活不过一炷香时间就会自爆。可万一它连重力都不按套路出牌呢?
想想就刺激!既然反粒子在电磁力、核力这些方面都唱反调,凭啥对重力就服服帖帖?要是哪天发现反物质会往上飘,那科幻片里的悬浮滑板说不定真能成。不过科学家们现在就像拿着放大镜找蚂蚁——连反氢原子都抓不住几颗,哪还轮得到测它们受不受重力影响啊!
之前咱们聊过暗物质像快递员般传递引力,暗能量像把宇宙当气球吹的隐身室友,今天这反物质活脱脱就是个镜中人。容易搞混很正常,毕竟这些概念听着都像从科幻小说里抄来的。但您可别误会,物理学家才不玩空想游戏——他们都是先在数学迷宫里摸到钥匙,再给这钥匙起个名字。就像程序员先写出代码,再给程序取名字一样。
所以啊,物理这门课可不是随便谁都能插嘴的。要是真想和物理学家掰手腕,至少得先学会他们那套数学摩斯密码。不过咱们普通人就当看魔术表演呗,跟着开开脑洞过过瘾也挺好。就像现在聊反物质,虽然搞不懂深奥的狄拉克方程,但不妨碍我们幻想开着反重力飞车去火星买菜对吧?这节反物质之旅就到这儿,咱们普通人就抱着爆米花看科学家们破解宇宙彩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