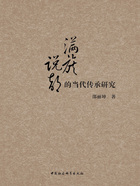
前言
一 研究价值与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满族说部传扬的英勇无畏地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黑暗、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舍生忘死地为国家安危、氏族生存奉献智慧与生命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等核心内容,与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内容高度契合,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说部主要功能是慎宗追远,讲唱满族说部,是满族先民弘扬自强不息、爱国爱族、骁勇坚忍的民族精神的重要方法;传承说部,是当代满族,特别是东北满族世家,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爱族、爱家教育的手段。而且满族先民的核心生活区域是祖国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的长期抗争和东北本土的其他族系民族的此消彼长的长期磨合过程中,在反抗俄、日侵略的浴血斗争中,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对满族说部当代传承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必然要对满族说部的传承特征、满族说部的传承人、满族说部与东北其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的比较及在当代的建构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既是满族说部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有助于满族说部在当下及未来的传承与保护,对于拓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构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方法
文献梳理法。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已经出版的三批“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内部刊物、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满族说部的资料以及传承人的录音带、访谈记录及各种手抄本等。
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目前被人类学、民俗学与民族学学科广泛使用。就本书而言,对“满族说部的当代传承问题”的关注离不开对传承人的调查及对当今传承方式的跟踪考察,田野调查的方法贯穿课题的始终。
统计学的方法。对一些采集的数据及根据文献梳理得来的数据,要适当地采取统计学的方法,比如通过表格或者绘图得出结果的方法,以便论点更加清晰明了。
三 满族说部研究概述
在“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大规模出版之前,满族说部曾以民间故事,或者神话等形式出版过。比如《尼山萨满》《天宫大战》和傅英仁讲述的《东海窝集传》,早就有所披露或出版。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满族说部的研究还很薄弱,早期的研究史其实就是搜集史:“满族说部的搜集情况不一,应始于20世纪初,此阶段跨度较大,从1900年一直到‘文革’结束。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的繁盛;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的沉寂;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满族说部的重现。”[1]
随着丛书的大规模出版及社会各界对满族说部的重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说部,对其研究可以说是一个逐渐走向深入与多元的过程,从最初只在个别专家学者的著作或者论文中见到关于满族说部的文章,到现在的丰富性与开拓性的见解,与几批“满族口头遗产系列丛书”的出版有密切的关系。截至2017年10月,满族说部已经出版三批丛书。满族说部自大批出版以来,竞相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其研究成果也取得了较好的影响。同时,满族说部立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以及其他级别的课题,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专著、论文,研究队伍日益壮大。
2008年以前,满族说部的文章多是对“满族说部”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介绍性与抢救性的文章,也有个别学者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比如周惠泉的《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王卓的《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富育光先生,作为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及研究专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为满族说部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以后,成果逐渐多元化,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满族说部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就以往的研究来看,由于满族说部的研究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满族说部这个称谓对于学术界也比较陌生,随着第一批、第二批满族说部丛书的出版,相关的学术研究陆续开展。截至2017年初,收录于中国知网的相关性论文及报纸的报道达百余篇。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富育光先生在1999年《民族文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这是较早的对何为“满族说部”、满族说部的性质与分类等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此外,富育光先生的《“满族说部”调查》,周惠泉先生的《论满族说部》《说部渊源的历史追寻与金代文学的深入研究》,王宏刚的《田野调查视野中的满族说部》,关纪新的《文脉贯古今源头活水来——满族说部的文化价值不宜低估》,高荷红的《满族“窝车库乌勒本”辨析》等,针对基本的概念和基本范畴等基础理论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和论述。2012年5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主编王卓的《满族说部的称谓与性质》,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满族说部的称谓与性质两个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满族说部的称谓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长篇口传叙事故事不同,不是本民族的语言而是汉语,并且是由满语称谓汉译而成。另外,被作为文学研究对象加以研究的满族说部,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是具有一定史诗性质的满族民间口传故事。除了对其基本概念进行理清,王卓主编对满族说部的分类问题也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并在《东北史地》上发表。依据满族说部调查、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奠基者,及满族说部的主要传承人富育光先生提出的三分法和四分法,王卓就掌握的几十本说部文本来分析,倾向于四分法。四分法的提出,有助于更细致地划分满族说部的类别。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日后深入地开展关于满族说部的研究工作。
第二,针对具体的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隋丽的《满族文化源头的性别叙事——以 〈天宫大战〉、〈东海窝集传〉 为例》一文以满族说部中的《天宫大战》和《东海窝集传》为研究对象,运用性别文化的阐释方法,探寻满族先民文化源头的性别叙事模式及其文化内涵。吕萍的《民族兴盛的历史画卷——论满族说部 〈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满族说部之佳作—— 〈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中提及,该书43万字,不仅内容丰富,形象生动,情节感人,而且在反映满族的历史、军事、风俗等方面,有如一部小百科全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谷颖的《满族说部 〈恩切布库〉 与 〈乌布西奔妈妈〉 比较研究》,两部作品都讲述了女神带领族人建立文明社会的艰辛历程,反映了满族先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通过对两部史诗的比较研究,能够清晰地辨识两位女神不同的性格特征,更能透视出史诗所反映的深刻文化内涵;《满族说部 〈恩切布库〉 的文化解读》,不仅展示了满族先人早期社会生活图景、宗教文化内涵,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文学作品;《满族说部 〈西林安班玛发〉 史诗性辨析》,《西林安班玛发》是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重要文本之一,它不仅承载了满族先民丰富的萨满文化,也在产生时代、文本形式、主体内容、传播流变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史诗性。2012年5月,江帆教授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满族说部对历史本文的激活与重释——以 〈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 为例》,文章通过对和满族说部有关联的历史本文与衍生的叙事文本之间关系的探析,阐释了历史本文怎样由满族说部的创作者创化为艺术叙事,以及满族说部叙事如何在与族群历史语境的互动中彰显出多元化的文化史意义。2013年,邵丽坤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发表的《〈天宫大战〉 与 〈恩切布库〉 之比较研究》,是对文本研究的进一步细致深入的探讨。
第三,满族说部中的神话研究,近些年来引起关注。较早对满族说部神话进行研究的文字出现在富育光先生出版的著作《萨满教与神话》一书中,对北方的萨满教创世神话、祖先英雄神话等进行了深入、翔实的论述,其中提及的《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就是萨满教中著名神话。近几年来的博士论文也出现了以萨满神话为选题的现象,如谷颖:《满族萨满神话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张丽红:《满族说部之女神研究》(吉林大学,2014年);李莉:《神话谱系演化与古代社会变迁——中国北方满—通古斯语族神话研究》(吉林大学,2014年)。几篇博士论文从不同视角切入,例如从神话学、原型批评理论等方面,运用文献解读和综合比较的方法,对满族神话进行深入研究,为满族说部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
第四,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富育光先生的《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一文中提到,满族世代根深蒂固的氏族祖先崇拜观念以及维系和凝聚氏族力量的精神支柱——穆昆制,是满族传统说部永葆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其得以传流至今的奥秘所在。凡讲唱本家族族源历史或家族英雄传奇类的说部,被原传袭家族视为祖传遗产,至今多由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后裔承继和保护,有清晰的传承谱系;大宗满族说部则包罗万象,涉及满族及其先世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是满族说部艺术流传的主流,有的具有几个朝代的传承史,成为北方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满族说部早期在民间靠满语传承与保护,晚清乃至民国以来,满语渐废,渐渐转变为以汉语汉文传播传承,两种语言文字的传承形式,都需要加以保护。高荷红的《关于当代满族说部传承人的调查》《满族说部传承圈的研究》,通过访谈传承人,对满族说部的传承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周惠泉、孙黎的《满族说部的历史渊源与传承保护》一文中说,根据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分类,满族说部属于第一类即民间文学。而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民间活态文学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中的崛起,将为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提供新的重要资源。为此,保护的意义十分重要,静态与动态的保护与传承要结合。2012年,何新生的论文《满族说部的活态展演》,也明确指出,满族说部毕竟是语言艺术,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料及文本上,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看还是很可惜的,因此,活态的传播与传承是当务之急。静态与动态结合的方式,必定会使满族说部得到更完整的保护。尤其是近几年来,邵丽坤以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中期成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主要围绕满族说部的当代传承问题展开,其中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满族说部需要多元化传承》;在《中国社科报》上发表的《创新满族说部的传承与发展》;在《满族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满族说部传承的危机及其在当代的建构》;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发表的《满族说部的传承模式及其历史演变》等,对满族说部传承方式的演变及在当代传承方式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陆续有学者关注满族说部的神话部分即“窝车库乌勒本”研究,比如王卓研究员的《论“创世”题材满族说部的文本体系》,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文中指出:“《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这四部‘窝车库乌勒本’文本,具有鲜明的体系化特征:《天宫大战》为创世神话,蕴含着诸多文化母题与故事原型,规定着其他文本的主题与人物及情节模式;《乌布西奔妈妈》为东海创世神话,主题上重复了《天宫大战》的创世与救世二重母题,情节模式上对《天宫大战》原型进行了置换变形,这一模式,为单独表现救世主题的《恩切布库》和《西林安班玛发》两个文本所再现,而且这个模式,还影响到《苏木妈妈》等其他一些满族说部的主题与情节结构。”对“窝车库乌勒本”的研究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荷红在其文章中早有专门的论述:《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研究——从天庭秩序到人间秩序的确立》(《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窝车库乌勒本”叙事特征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窝车库乌勒本”与满族文化关系研究》(《满族研究》2013年第3期);《满族萨满史诗“窝车库乌勒本”研究》(《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长春师范学院的谷颖的博士论文《满族萨满神话研究》,把“窝车库乌勒本”作为满族萨满神话的一部分研究。近年来,高荷红博士集中就满族说部的记忆与书写问题进行研究,主要代表性成果有《记忆·书写:满族说部的传承》(《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从记忆到文本:满族说部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等。
另外,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工作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有国家的基金立项和支持,学者们也陆续发表了论文。满族说部的部分内容也逐渐被纳入民族典籍的翻译工作中。大连民族学院外语学院刘艳杰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英译研究——以满族说部之创世神话 〈天宫大战〉 英译为例》一文,通过对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的英译研究,来探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目的、方法以及策略等一系列问题。大连民族学院教育学院的田春燕的论文《浅议少数民族文学典籍英译中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补偿——以 〈尼山萨满〉 英译为例》,对宗教因素在《尼山萨满》英译中的作用进行探讨,以此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工作。满族说部的英译典籍翻译工作在逐渐开展与深入,当然,满语文的翻译工作,一直是最直接的问题。黑龙江大学满语言文化中心的鄂雅娜的论文《满语文学翻译中语境的作用——以 〈尼山萨满〉 为例》一文,通过对《尼山萨满》两种汉译本诸多实例的对比和分析,来探讨语境对满语文翻译的作用和影响,而且,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倾向性的差异导致翻译的不同。
截至2017年,共出版三本专门研究满族说部的文集。2009年,富育光先生主编的《金子一样的嘴——满族传统说部文集》,在学苑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录了2009年以前,发表在国内期刊和报纸上有关研究和评述满族说部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并汇集成书。富育光、王兆一、周惠泉、曹保明、郭淑云、郎樱等国内知名学者的论文都在此列。此外,也有学术新人的研究成果。该书可以说是研究满族说部初始阶段的代表性成果,对满族说部的基本定义及基本理论问题有了初步的探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和说部的传承与保护问题都有涉猎。近几年来,《满族古老记忆的当代解读——满族传统说部论集(第一辑)》和《满族传统说部论集(第二辑)》出版,这两部论文集对满族说部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从多个视角与领域深化了满族说部的研究。
其中,《满族古老记忆的当代解读——满族传统说部论集(第一辑)》(长春出版社2012年版)与满族说部学会的成立密切相关。2011年8月9日,“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成立暨首届满族说部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发言的论文把满族说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会后,经过满族说部学会部分成员的辛勤努力,整理出版了文集第一辑。从该文集收录的论文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对满族说部研究取得较为突破性的进展。文本研究进一步拓展,除了对具体的文本《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天宫大战》等进行细致的分析解读外,也对满族说部的组成部分“定场歌”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其次,历史文化研究继续深入,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于从海洋文化的角度对满族说部进行了研究。此外,理论构建方面也有一定进展。王卓研究员在富育光等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满族说部基础理论的研究论文,对满族说部的称谓、性质以及分类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有益的探讨和研究。该文集可以说是近年来满族说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2016年,满族说部学会推出《满族传统说部论集(第二辑)》。
近年来,关于满族说部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其中,201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荷红博士的著作《满族说部传承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满族说部传承研究》一书是对满族说部全景式的研究,涵括了从满族说部相关概念的界定到满族说部搜集史的研究,从满族说部传承人、传承方式的研究到满族说部文本情况的介绍。作者并结合多次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和满族说部传承的特殊性,在此书中提出了“书写型”传承人的概念,阐述了满族说部传承圈及文化圈之间的关联。我们发现,伴随着满族在历史、社会乃至文化上的巨大变迁,满族说部的传承衍生出独特的演化模式:由口传到书写的转变,从氏族秘传到共同地域的广泛传递,由满语演唱到满汉混合语的演述,从而实现多族群的共享。该书通过大量的田野访谈和田野研究,31位满族说部传承人的生平及传承经历得以较圆满地呈现,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此外,2016年,长春出版社推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满族说部系列研究丛书”,其中有《满族说部文本研究》《满族说部口头传统研究》和《满族说部英雄主题研究》,有评论者说:“捧读丛书,笔者认为这是一部既具有历史厚度,又具有文化热度的研究佳作。首先,具有浓厚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次,具有鲜明的理论前沿意义。再次,具有材料搜集翔实、内容安排恰当、条分缕析的内容属性。最后,洋溢着浓厚的现实关怀,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2]另外,王卓、邵丽坤的《满族说部概论》,于2014年12月出版,主要是对满族说部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集中、细致的梳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杂志社主编王卓研究员于2013年3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研究》一书,同时该书也被列为“东北文化研究丛书”。该书所论及的既有民间文学又有作家文学,既有对清代东北地域满族文学的论述也有山海关内外满族文学的比较。作为古老的长篇口传文学——满族说部,被放置在清代东北满族文学大的框架之中,提出在清代东北满族的文学生活并没有从日常生活当中独立出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满族说部记载了大量满族民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是口传形态的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综合形态。该书为满族说部研究提供了清代满族文学的完整学术框架,讨论了满族说部的称谓、性质、分类等基础理论问题,为满族说部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规范;还依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和性质,确定了已经出版的28部满族说部的产生时间和归类。该书的论据除了依据历史文献和文本分析,还引入作者童年时期作为满族说部聆听者的个人经验,独特的视角与方法,使得该著作独树一帜。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杨春风,于2013年3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这部专著视域较广阔,在研究满族说部中所反映的各朝代的民间历史文化记忆时,注意了同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的官方文献之间的比较,使书面的、官方的历史记载与口头的、民间的历史记忆之间互相印证,彼此补充,不但加深了满族说部的可信度,而且充分说明满族说部具有的历史价值,对正史起到补充的作用。
2013年3月,郭淑云教授的《〈乌布西奔妈妈〉 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项目。《乌布西奔妈妈》是满族先世女真时期流传下来的著名萨满史诗,流传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东海女真人之中。鉴于《乌布西奔妈妈》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作者力图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史诗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等多学科视野下的观照,从不同的学科全方位解读《乌布西奔妈妈》的价值与意义。该书共分为九个章节,内容包括:《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性及其特点,《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采录、整理与研究,《乌布西奔妈妈》与东海女真人的历史文化渊源,《乌布西奔妈妈》与部落社会,《乌布西奔妈妈》与萨满,《乌布西奔妈妈》与萨满文化,《乌布西奔妈妈》与渔猎文化,《乌布西奔妈妈》与航海活动,《乌布西奔妈妈》的文学性解读等内容。
满族说部研究同时获得国家的多项课题立项。较早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有郭淑云的“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研究”,仅就这几年的立项成果来看,主要有辽宁大学江帆教授的“满族说部研究:叙事类型的文化透视”获得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荷红的“口述与书写:满族说部传承研究”,获得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东北史地》杂志主编王卓研究员申报的“满族创世神话谱系及其历史演变研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杨春风研究员申报的“满族说部中的神话与史诗研究”,同时获得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文学类立项;2014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员邵丽坤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立项,申报题目为“满族说部的当代传承研究”。
满族说部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研究会有不同的发现。例如杨春风的论文《从“满族说部”看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解体》《满族说部中的肃慎族系婚俗》,苏静的《满族说部“收服英雄”母题研究》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看出说部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母体。而且,由于满族说部具有文艺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必将为人类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尽展风采,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说部的研究视域与理论深度会更上一层楼。
通过对满族说部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满族说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价值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保护与传承研究、记忆与书写等方面,但是对满族说部的当代传承问题,还较少有专门细致的学理性的分析与探讨。本书以“满族说部的当代传承研究”为切入点:第一,将满族说部的核心精神放在中华优秀文化的框架之内,赋予满族说部传承新的意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第二,从传承方式及特征、传承人、满族说部的传承模式在当代的探索及演变几个方面,集中进行探讨;第三,首次对满族说部的当代传承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对满族说部传承体系的当代建构提出在保护传统传承方式的基础上,进行教育传承及多元化传承等的探索和大胆进行开发性传承的意见与建议。
[1]高荷红:《满族说部搜集史初探》,《满语研究》2008年第2期。
[2]赵楚乔、修然:《立体研究系列梳理——简评“满族说部研究丛书”》, 《光明日报》2017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