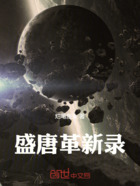
第6章 丝路星火
永徽元年冬,当第一场雪落在长安城头,杜家商团的驼队正穿越葱岭。领头的骆驼背上,载着林砚之亲自设计的“测绘仪”——用磁石罗盘、圭表和齿轮组成的装置,可精准测量经纬度。商队首领杜明远摸着腰间的双鱼符信物,望着前方的雪山,想起三个月前少东家的叮嘱:“找到波斯的‘圣火教’,他们守护着墨门早年流传的‘神火秘典’。”
与此同时,长安神机监的工坊内,林砚之正在调试“硫化橡胶”。当乳胶与硫磺在青铜釜中熬煮,渐渐变成黑色的弹性物质,砚礼突然指着冷凝管:“哥,气泡变密了!”他点头,取出制成的橡胶密封圈,按在蒸汽管道接口——滴水不漏。
“现在,蒸汽压力能提升至五斤每寸。”他对韦弘机道,“新木鸢的载重量可增至三百斤,足够搭载两名士兵和神火弩。”说着,他展开波斯地图,上面用朱砂标着“巴赫拉姆火神庙”——传说中保存着墨门早期的火药配方。
腊月廿三,灶王节。铁匠铺里,母亲正在烙胡饼,父亲握着新制的“曲辕犁改良版”,忽然长叹:“你祖父若看见如今的匠户能入朝为官,该多欣慰。”林砚之望着墙上新增的墨门纹章,想起李治亲书的“百工兴国”匾额,忽然听见巷口传来喧哗——十余名西域胡商抬着巨大的木箱,箱角刻着熟悉的齿轮纹。
“林监丞,”为首的胡商跪拜,“波斯圣火教大主教让我们带来此物,说与墨门有缘。”木箱打开,竟是半具青铜浑天仪,表面刻着星图与波斯文,中央的齿轮组与地宫的地动仪如出一辙。杜挽月忽然惊呼:“这是傅奕当年送给波斯王子的‘天象仪’!”
浑天仪底部,刻着一行小字:“永徽元年,当木鸢飞临波斯,圣火将重燃墨门之光。”林砚之摸着冰凉的青铜,忽然想起地宫壁画上,傅奕与波斯使者交谈的场景——原来,墨门的火种早已沿着丝绸之路播撒。
正月初七,新木鸢试飞升空。这次它搭载了完整的蒸汽动力系统,尾部喷口喷出的火焰呈稳定的蓝色,机身两侧增加了“副翼”——用橡胶制成的可动翼面,能通过磁石罗盘远程控制。当木鸢在长安城上空盘旋,百姓们纷纷跪地叩拜,将其视为“神鸟”。
然而,喜悦背后是危机。长孙无忌的密探传来消息:突厥余部与吐蕃结盟,计划从河西走廊突袭,而他们的秘密武器,正是从波斯购得的“神火投石机”——能将燃烧的硫磺块抛射百步,威力不下于唐军的神火弩。
“投石机的关键在抛物线计算。”林砚之对薛仁贵的使者说,“给我三日,可制‘弹道测算仪’,让神火弩的射程超过投石机。”他取出从浑天仪拆解的齿轮组,结合《九章算术》的勾股定理,制成可调节角度的瞄准器,“记住,仰角四十五度,射程最远。”
与此同时,杜挽月带着商队抵达波斯,在巴赫拉姆火神庙见到了大主教。对方取出用金箔包裹的《神火秘典》,里面记载着墨门巨子早年在波斯的实验:“以硝石七、硫磺二、木炭一,合以橄榄油,可得猛火油。”这与林砚之改良的火剂配方不谋而合。
“大主教,”杜挽月展示双鱼符,“墨门在东方重燃神火,愿与波斯共享技艺,让火光照亮丝路。”她递出活字印刷的《墨经》片段,以及硫化橡胶制成的密封圈,“此物可让贵国的火神庙机关永不漏水。”
三月,西域传来捷报:薛仁贵使用弹道测算仪,在敦煌城外重创吐蕃投石机部队,神火弩的箭矢如雨点般落入敌阵,连吐蕃赞普的金顶大帐都被点燃。与此同时,波斯使者随杜家商团抵达长安,向李治献上“圣火锦旗”,上面绣着齿轮与火焰交织的墨门纹章。
长安城里,神机监的工坊日夜通明。林砚之带着匠人们将活字印刷术改良为“雕版与活字结合法”,既能批量印刷,又可灵活排版。当第一本完整的《唐本草》活字版问世,李淳风惊叹:“从此,医书可遍传州县,百姓皆得良方。”
更深露重时,林砚之独自来到地宫。新扩建的密室里,存放着从波斯带回的神火秘典,以及杜挽月在矿洞发现的“墨门星图”——上面标注着木鸢飞行的最佳气象条件。他摸着墙上新增的匠人画像,杜明远、波斯大主教、甚至砚礼都在其中,忽然明白,墨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人之力,而是无数匠人的心血汇聚。
“哥,”砚礼抱着新制的“蒸汽钟表”进来,齿轮的轻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波斯使者说,他们的王子想学习木鸢制造。”林砚之笑了,接过钟表:“那就让他们来长安,让丝路的星火,照亮更多地方。”
窗外,长安城的灯火如星河般璀璨,木鸢的剪影偶尔掠过夜空,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标志。林砚之知道,接下来的路还很长——要改良蒸汽动力,要完善活字印刷,要让墨门的技艺深入每一寸土地。但他并不孤单,有杜挽月的商队横跨丝路,有韦弘机的将作监遍寻古迹,有天下匠户的同心协力。
永徽元年的冬天即将过去,新的春天正在孕育。当第一缕春风吹过终南山,木鸢的翅膀将再次展开,带着盛唐的文明,飞向更广阔的天地。而林砚之,这个来自未来的理科生,正用双手,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属于革新者的篇章——不是改写,而是让文明的星火,燃烧得更加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