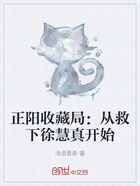
第34章 煤炉旁的算盘声
正阳门的积雪未消,小酒馆的煤炉却少见地冷了下来。徐慧真望着空荡荡的八仙桌,蓝布围裙下的手指无意识绞着红绒布——那是静理新做的算术本封皮。范金有坐在吧台前,中山装口袋露出半截酒票,正对着赵会计的账本指手画脚,鼻尖还沾着今早赊的二锅头酒气。
“公私合营嘛,”他的钢笔尖敲着“服务员”一栏,墨水在泛黄的账页上洇出小团,“就得有个国营的样子,”他斜睨着站在煤炉旁的何玉梅,蓝布衫洗得发白的领口跟着抖动,“小何,把‘徐记小酒馆’的牌子摘了,换成‘正阳门第一饮食合作社’。”
徐慧真的银戒指“当啷”磕在吧台上,惊飞了煤炉上的麻雀:“范经理,”她指着墙上静理用蜡笔写的“童叟无欺”,字迹歪歪扭扭却带着温度,“李区长剪彩时说过,要保留老字号招牌……”
“李区长?”范金有的钢笔尖在“公私合营”四个字上划出三道重痕,中山装袖口的补丁跟着晃了晃,“现在是街道办直管,”他忽然压低声音,眼神扫过空荡荡的天井,“慧真啊,你男人贺永强的事我还帮你瞒着,那可是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煤炉的铁壶突然“咕嘟”作响,牛爷的旱烟袋“啪”地敲在石桌上,惊得赵会计的的确良衬衫抖了抖:“范主任,”他故意把“主任”二字咬得发脆,铜烟锅里的火光映着镜片,“小酒馆开了十年,头回听说喝酒还要人端碗,”他指向何玉梅手中的搪瓷盆,“当年琉璃厂的荣宝斋,客人都是自己拎着酒坛上楼的,讲究的就是个自在。”
范金有的脸涨成紫茄子,钢笔尖在账本上戳出个洞。他忽然看见苏浩然的帆布包闪过月洞门,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苏老师来得正好!”他堆出笑脸,中山装口袋里的酒票窸窣作响,“您给评评理,公私合营要不要改革?”
苏浩然站在月洞门旁,看着吧台上摊开的新账本,系统界面闪烁**「检测到经营危机(稀有度★★)」**,红色警告在视野边缘跳动。他摸着帆布包上的青铜钥匙,钥匙扣是牛爷送的老铜锁改的:“范主任,”他的目光扫过墙上静理画的小马,“故宫修文物讲究‘修旧如旧’,小酒馆的老规矩,何尝不是老BJ的烟火气?”
范金有噎住了,喉结在磨破的衣领下滚动。赵会计的算盘珠子突然响了,她指着“招待费”一栏,指甲盖大小的钢笔字密密麻麻:“范经理,您这三天签了七张酒票,按规定……”
“记公账!”范金有猛地合上账本,震得吧台上的醋壶歪了歪,“公私合营嘛,公方经理自然要招待客人,”他忽然看见徐慧真走向煤炉,汤勺碰撞锅底的声音格外清脆,“慧真,去把牛骨汤的秘方交出来,以后由公家统一熬制。”
徐慧真的手停在汤勺上,蓝布围裙下的身子绷得笔直。她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用布满老茧的手握着她的手:“汤锅里熬的不是骨头,是人心。”银戒指在煤炉光下闪过,她转身时已换上笑脸:“范经理,秘方是祖上传的,”她指向静理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的背影,“要不您问问李区长,非遗秘方能不能入公账?”
范金有的钢笔尖断了墨水,他忽然想起剪彩那天李区长拍着徐慧真的肩膀,说要把小酒馆打造成“文化窗口”。他抓起账本起身,中山装后襟沾着煤炉的灰:“先记着,”他撞翻了何玉梅端来的空碗,“我去街道办汇报工作。”
煤炉的热气裹着酒香漫进天井,苏浩然望着范金有的背影,帆布包带扫过静理的算术本。他凑近徐慧真,压低声音:“慧真姐,账本让赵会计按旧例记,”他指向墙上被积雪覆盖的“徐记”匾额,“我明天带北大学生来写生,就画这煤炉旁的算盘——公私合营不是拆旧墙,是给老房子添新瓦。”
徐慧真的眼睛亮了,蓝布围裙下的手指终于松开红绒布。她舀起一勺牛骨汤,当归的药香混着牛油的醇厚在煤炉上方盘旋:“苏老师放心,”汤勺在粗瓷碗里转出个漂亮的弧,“汤里的当归还是三钱,党参还是五钱,”她忽然笑出声,眼尾的细纹里盛着暖意,“就是范经理的酒账,得按市价算——公家的钱,也不能白喝我的汤。”
暮色漫进小酒馆时,何玉梅蹲在煤炉旁拨弄炭灰,蓝布衫上落着细小的火星:“赵姐,这月怕是要亏空了,”她望着空荡荡的酒坛,“以前徐老板一人就能顾过来,现在多了我们俩,反倒没人来了。”赵会计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忽然看见徐慧真往账本里夹了张纸条——是苏浩然用修画的宣纸写的“非遗保护申请草案”,边角还画着牛骨汤的简笔图。
“小何,”徐慧真递过热汤,碗沿还带着煤炉的温度,“明天把静理的算术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她指向天井里的老槐树,枝桠在暮色中划出沧桑的轮廓,“北大的学生要来画老槐树,说不定能给小酒馆招些新客。”
雪又开始下了,范金有的自行车铃在胡同里响得慌张,链条在结冰的路面上打滑。苏浩然站在“经纬堂”门口,看着小酒馆的灯光透过结霜的玻璃,暖黄的光晕里,徐慧真正用父亲留下的老算盘拨弄珠子,黄花梨的算珠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他忽然懂了——徐慧真的隐忍不是妥协,而是像煤炉里的炭火,表面暗红,内里却藏着不熄的热。
“苏老师,”徐慧真的声音从雪幕中传来,老算盘在她手中发出轻响,“范金有把算盘锁进了保险柜,”她的银戒指映着月光,“不过没关系,我这儿还有把父亲留下的老算盘,珠子是黄花梨的,比公家的算盘多两道梁。”
苏浩然转身,看见她捧着老算盘走来,蓝布围裙上落着雪花。那算盘的木纹与四合院的老槐树相似,每颗珠子都磨得发亮,穿档的棉线换过三次,却依然结实。他忽然想起石老的话:“真正的修缮,是让老物件在新日子里继续呼吸。”
“慧真姐,”他摸着算盘的穿档,指尖划过刻着“民国廿三年”的边框,“明天让北大学生给这算盘写篇论文吧——每道木纹里,都藏着小酒馆的经纬,就像您熬汤的火候,多一分太旺,少一分太弱,全在人心。”
雪越下越大,小酒馆的煤炉重新旺起来,汤锅里的牛骨“咕嘟”作响,把积雪都烘出了暖意。徐慧真的老算盘摆在吧台上,与范金有的新账本并排而立,就像正阳门的青砖与新刷的红漆,在时代的风雪里,共同勾勒着属于小酒馆的经纬图。赵会计忽然指着账本惊呼:“徐经理,苏老师带学生订了二十碗牛骨汤!”何玉梅的蓝布衫在煤炉旁闪过,静理的算术本被小心地挂在“徐记”匾额下,纸页上的“1+1=2”与老算盘的算珠相映成趣。
范金有的自行车滑过结冰的胡同,口袋里的酒票被雪水洇湿,模糊了上面的公章。他不知道,此刻小酒馆的老算盘上,徐慧真正用父亲教的“九归诀”,在公私合营的账本上,算出了一笔属于老匠人的精明账——那是比任何改革都更坚韧的生存智慧,就像煤炉里的炭火,永远在时代的风雪里,煨着一碗热汤的温度,等着懂它的人推门而入,在八仙桌旁坐下,听着算盘响,闻着汤香,把日子喝出滋味来。
雪停时,小酒馆的门“吱呀”推开,强子的三轮车夫带着满身雪气进来,身后跟着几个戴校徽的学生。徐慧真的老算盘珠子又开始跳动,这次算的不是亏损,而是北大学生们点的牛骨汤份数。煤炉的火光映着她的蓝布围裙,就像映着无数个清晨与黄昏,小酒馆在时代的洪流里,始终守着那碗热汤的温度,还有老算盘里的人间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