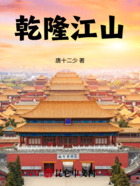
第5章 新火烹旧油
养心殿西暖阁,地龙依旧烧得旺,驱不散腊月的寒意,也驱不散新帝弘历眉宇间那层冰霜。允禄被革爵圈禁、家产查抄的消息,如同在滚油里泼了一瓢冷水,瞬间炸翻了整个朝堂。惊恐、猜疑、观望的气氛,比殿外的风雪更刺骨。
张廷玉垂手立在御案左下首,眼观鼻,鼻观心。对面的大学士鄂尔泰,花白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几次欲言又止。暖阁内,只剩下弘历翻阅奏章时纸张摩擦的沙沙声,以及更漏滴水的单调声响,压得人喘不过气。
终于,弘历合上一份奏本,指节在光滑的紫檀木案面上轻轻叩了两下,打破了沉寂。他抬眼,目光平静地扫过两位重臣。
“衡臣公,鄂尔泰。”弘历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在暖阁内回荡。
“臣在。”两人同时躬身。
“允禄贪渎的窟窿,查得如何了?”弘历的目光落在张廷玉身上。
张廷玉上前半步,声音沉稳:“回皇上,庄亲…允禄府邸已查封完毕。初步清点,除御窑贡瓷、逾制之物外,现银、金器、田契商铺折价,约莫…一百二十万两有余。”
鄂尔泰忍不住插话,语气带着愤慨:“皇上!仅现银就抄出三十余万两!这还不算他京郊那几处占地千亩的庄子!一个亲王,岁俸不过万两白银,万斛禄米!他这金山银海,分明是蛀空了国帑民脂!”
弘历脸上没什么波澜,只淡淡问:“通惠河那二十万两亏空呢?”
张廷玉微微一顿:“据允禄府上账房供述及工部账目比对,确有二十万两漕银…流入了允禄私囊。其余亏空…尚在追查关联人等。”
弘历点了点头,目光转向堆积如山的另一摞奏章:“这些,是各地督抚的请安折子,还有…要钱的折子。”他随手拿起最上面一份,翻开,“陕甘总督奏报,去岁大旱,今春恐有饥荒,恳请拨粮三十万石,银五十万两以赈灾抚民。”
他又拿起一份:“云贵总督密奏,缅甸土司蠢蠢欲动,边境哨所年久失修,请拨饷银二十万两,加固边墙,增补军械。”
再一份:“直隶总督奏,永定河数处堤坝去年已被冲毁,今春桃花汛在即,若再不抢修,京畿恐遭水患,请拨工料银四十万两…”
弘历将奏章轻轻丢回案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抬眼,目光如寒潭深水,看向张廷玉和鄂尔泰。
“允禄抄出来的银子,杯水车薪。国库…朕登基前便已看过密档,寅吃卯粮,空虚得很。皇考厉行峻法,耗尽了元气,也绷紧了弦。朕登基,诏告天下‘以宽为政’,这弦,得松一松。”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那块冰冷的田黄镇纸,“可这松,不是放任自流。灾要赈,河要修,边要固…银子,从何而来?”
鄂尔泰眉头紧锁,拱手道:“皇上,开源节流乃千古不易之理。臣以为,当务之急是严查贪墨,追缴亏空,如允禄之流,务必深挖严惩,以儆效尤!同时,裁撤冗员,削减宫中不急之务,总能挤出些银子来…”
弘历嘴角勾起一丝极淡的弧度,似是讥讽:“深挖严惩?鄂尔泰,允禄是皇叔,是顾命亲王!动他一个,已是朝野震动!再深挖下去,你想把这满朝文武,宗室勋贵,都挖个底朝天吗?朕这‘以宽为政’的旗号,还要不要打了?”
鄂尔泰被噎住,脸涨得通红:“皇上!可是…”
“没有可是!”弘历的声音陡然转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贪墨要查,但不是现在!也不是用这种刮地皮的法子!朕要的是…一个能解燃眉之急,又不至于动摇朝局根本的法子。”
他的目光,锐利如鹰隼,最终牢牢锁定了沉默的张廷玉。
“衡臣公,”弘历的声音放缓了些,却带着更深的试探和压力,“你是三朝老臣,执掌户部多年,管过钱粮,理过漕运,最知朝廷运转之艰。依你之见…有何良策?”
暖阁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鄂尔泰也看向张廷玉,眼神复杂。
张廷玉只觉得后背的冷汗又渗了出来。新帝的目光,像两把烧红的锥子,要把他钉穿。他知道,这个问题,避无可避。他缓缓抬起头,迎向弘历深不见底的眼眸,声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的沙哑:
“皇上…臣…斗胆一言。国用匮乏,无非开源节流。节流非一日之功,且易生怨望。开源…加赋加税,更是动摇国本,万不可行。”他顿了顿,仿佛下定了极大的决心,“臣…思得一策,或可…权宜之计。”
“讲。”弘历身体微微前倾,眼神专注。
“臣观前明旧档及本朝事例…官员犯有过失,或罚俸,或降级,或罢官,于朝廷而言,不过失一可用之才,于国库而言,并无补益。”张廷玉字斟句酌,语速缓慢,“若…若效仿前朝某些成例,允其…以银赎罪。视其过失大小、官职高低、家资厚薄,定下相应‘议罪’银两数额。所缴之银,不入内帑,专设一库,直归户部,用于军国急需。如此…一则,可保全官员体面,使其戴罪留任,为国效力;二则,朝廷可得实银,以解燃眉之急;三则…亦可稍缓‘以宽为政’下,吏治或有松弛之忧。”
“议罪银?”鄂尔泰失声惊呼,眼睛瞪得溜圆,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张中堂!此…此议太过荒唐!以银赎罪?那国法何在?纲纪何存?长此以往,岂非明码标价,纵容贪渎?有钱便可免罪,无钱便要受罚?天下士民将如何看待朝廷?!”
张廷玉面色不变,只微微侧身,对着鄂尔泰拱手:“鄂中堂稍安。此议…自然有其弊端。然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此法关键在于‘度’与‘制’。所议之罪,当限于非十恶之过失;所缴之银,数额须有定规,不可随意;其用途,必须透明,专款专用,接受都察院稽查。此乃权宜,非为定制。待国库稍裕,吏治澄清,自当废止。”
鄂尔泰气得胡子直抖:“权宜?此乃饮鸩止渴!一旦开口子,后患无穷!张中堂,你…你岂能出此下策!”
弘历没有理会鄂尔泰的激动,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张廷玉脸上,仿佛在剖析他每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暖阁内陷入一种微妙的僵持。
半晌,弘历才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以银赎罪…保全官员体面,朝廷得实银解急…衡臣公,此议…倒也新奇。”他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鄂尔泰所言,亦有其理。此法,确实易开贪渎之门,坏朝廷法度。”
张廷玉心头一沉。
弘历话锋却陡然一转:“然,国之急难,迫在眉睫。陕甘灾民嗷嗷待哺,永定河堤摇摇欲坠,缅甸土司虎视眈眈…朕,等不起鄂中堂那深挖严惩、裁撤冗员的慢药!”他的语气陡然加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衡臣公此议,虽有瑕疵,然于当前情势,不失为一条…可解燃眉之急的路径!”
鄂尔泰脸色煞白:“皇上!三思啊!”
弘历抬手,止住鄂尔泰的话头,目光灼灼地盯着张廷玉:“衡臣公,既然是你提出此议,想必已有章程。朕命你,三日内,拟出‘议罪银’细则奏来!所议之罪范围、银两数额等级、收缴流程、监管稽查之制,务必详尽周密!记住,此乃权宜之计,务必严防流弊!若有差池…”弘历的声音冷了下来,“唯你是问!”
张廷玉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头顶。他知道,自己递出去的,是一把双刃剑,而握剑的人,是这位心思深沉的年轻帝王。他深深躬身,掩去眼底的复杂情绪:
“臣…张廷玉,领旨。”
鄂尔泰看着张廷玉领旨,又看看御座上面无表情的弘历,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颓然低下了头。
弘历挥了挥手:“都退下吧。张廷玉留下,朕还有事交代。”
鄂尔泰欲言又止,最终只能躬身告退,背影带着说不出的萧索。
暖阁内只剩下弘历与张廷玉两人。烛火跳跃,将两人的影子拉长投在墙上,沉默而压抑。
“衡臣公,”弘历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更深沉的意味,“你方才说,此乃权宜之计?”
“回皇上,确是权宜。”张廷玉谨慎回答。
“权宜…”弘历咀嚼着这个词,目光落在窗外呼啸的风雪上,“但愿…它真能解了这燃眉之急。只是这‘油’…”他收回目光,再次看向张廷玉,那眼神锐利得仿佛能穿透人心,“…烹起来,火候若掌握不好,烧焦了锅,也是常事。衡臣公,你是老成谋国之臣,这火候…就由你替朕,好生看着吧。”
张廷玉只觉得喉头发紧,深深一揖:“臣…明白。定当殚精竭虑,不负皇上所托。”
他退出养心殿,凛冽的寒风如同冰冷的鞭子抽打在身上。抬头望去,紫禁城依旧笼罩在无边无际的风雪之中。允禄的倒台,是烈火烹油;而这“议罪银”的出炉,又何尝不是将整个官场架在了新的火上?新火烹旧油,这锅,才刚刚烧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