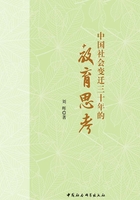
二 课程体系转轨的基础
在现代课程理论的视野中,社会、儿童、学科是三个基本要素。20世纪以来,围绕学校课程的设计有“学科中心论”“儿童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几派主张的争论,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来解释课程的功能、结构、内涵等问题[4]。他们所着重的三个角度无疑都是设计课程时不可或缺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把“上面说明的三种观点都考虑到。这三种观点的每一种虽然都不完全,但是都可能对设计一套完整的课程作出某种贡献”[5]。从我国设计普通中学课程的思路来看,对于学科的逻辑结构、儿童的心理序列考虑较多,也较成熟,而对课程的“社会效用”(即满足社会期望和社会需要的程度)缺乏深刻的思考,造成课程体系与社会需求的不合拍。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设计课程体系的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极不平衡,从西部到东部展示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不同时期的风貌。各地的城乡之间差异悬殊,城市机器轰隆的工业化景观与农村刀耕火种的自然经济状态成鲜明对比。就农村而言,差异也是惊人的。农村2000多个县中平原县占26.5%,山区县占39.6%,丘陵县占33.9%。农村经济发展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计算,最高的县与最低的县相差10倍以上。
这种差异性意味着各地区对劳动后备军的素质、规格、类型的要求也不相同。因而,各地对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即将流入劳务市场的普通中学学生所受教育内究的要求不可能千篇一律,试图用统一的课程体系框架所有普通中学的做法显然会受到现实的诘难。上海等大城市需要的劳动后备军是具备基础科学技术知识的熟练工人,农村地区则需要有一定农业知识技能可以胜任当地农、林、牧、副、渔生产的新型农民。明智的选择是建构适应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特点的多元课程体系。
此外,地方对促进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人才的需求以及地方对教育的投入也是由“一元”课程体系向“多元”课程体系转轨的基础。众所周知,由于国力所限,我国不可能对教育投入大包大揽,教育经费的相当部分需要地方集资、投资,农村教育尤其如此。地方对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及投入量显然与教育能为地方培养人才的数量、质量成正比。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战略一直是国家统一计划、统一培养、统一使用。统一的课程体系与此是相匹配的。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注重整体利益而忽视局部利益。就县、乡普通中等教育而言,它们每年为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输送了一批批人才,而毕业后返乡为当地服务者却寥寥无几。同时,大部分迈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就业者,由于不具备一定的生产知识技能,进入生产领域后显示不出教育投入的效能。地方投入人力、财力办教育,而培养出的人却不能为当地社会进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教育投入的低效益势必会影响地方对教育再投入的积极性。这对个体而言也是如此。农民对教育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看到子女在学校所学知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变化。有人对回乡初中毕业生的调查表明63.5%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生产劳动值低于当地平均水平[6]。当家长们看着“升学”无望、“致富”无术的子女悻悻而归时,他们会怎样伤心,他们何以能产生“积极办学”的热情呢?因此,当我们指责地方政府和家长不愿投资教育的短视行为时,是否应反思一下教育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学校的课程如果不能紧扣现实社会的脉搏,不能给予个体适应社会和求得自身更高发展的本领的话,则这种课程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就发生了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