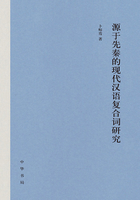
五、研究材料的选取
本书选取《辞源》(修订版合订本)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现汉》)作为研究语料的来源。选取两本辞书对比的原因如下:
《辞源》的编纂开始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915年以甲乙丙丁戊五种版式出版,1931年出版《辞源》续编,1939年出版《辞源》合订本。新中国成立后,读者迫切需要一部内容充实的古汉语词典,因此,1958年开始了《辞源》修订工作,并根据与《辞海》《现汉》的分工原则,拟将《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我们一般把修订以前的称为旧《辞源》,将后者称为新《辞源》。两版《辞源》在性质和词目收录等方面略有不同。
旧《辞源》主编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一文说明了其编纂意图:
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欲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则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征文考献,反不如寄居异国。其国之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毁弃一切,以言革新,又竟以旧学为迂阔。新旧扞格,文化弗进,友人有久居欧美,周知四国者,尝与言教育事,因纵论及于辞书,谓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吾国博物院图书馆未能遍设,所以充补知识者莫急于此。且言人之智力因蓄积而不得其解,则必疲钝萎缩,甚至穿凿附会,养成似是而非之学术。古以好问为美德,安得好学之士,有疑必问,又安得宏雅之儒,有问必答,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其语至为明切。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当始事之际,固未知其劳费一至于此也。
从上边的说明中可见《辞源》产生的历史原因。一是由于十九世纪的西学东渐,随着西方知识传入中国,自然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新义,只有正确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才能够使更多的人接受新知识新文化。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废弃和国外留学人员的增多,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强度大大降低,导致一批新的学人面对中国之书则不知所云为何,“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征文考献,反不如寄居异国”,阻碍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这两种因素导致“新旧扞格,文化弗进”,成为开启民智的障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急需一本辞书辅助中西文化的交流。
另外,《辞源》虽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但吸收了现代辞书的特点,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首先,它突破了中国古代以字为训释的对象,而是将词语的释义作为训释的起点。“凡读书而有疑问,其所指者字也,其所问者皆辞也。……故有字书不可无辞书,有单辞不可无复辞。此书仍以新字典之单字提纲,下列复辞,虽与新字典同一意向,而于应用上或为较备,至与字书之性质,则迥乎不侔也。” 其次,《辞源》注重词义的孳乳和源义的探求。“始知沿流以溯源,不如由源以竟委。……同人以此自励,源之一字,遂日在心目。当此书刊布预告之际,方考订日有所获,因遂以名其书。”
其次,《辞源》注重词义的孳乳和源义的探求。“始知沿流以溯源,不如由源以竟委。……同人以此自励,源之一字,遂日在心目。当此书刊布预告之际,方考订日有所获,因遂以名其书。” 因此,《辞源》在列举书证时力求找到词语在典籍中的首见时代,这项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艰巨的。
因此,《辞源》在列举书证时力求找到词语在典籍中的首见时代,这项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艰巨的。
这种历史条件和编纂意图,决定了《辞源》选词释义的原则,即“《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了现代辞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结合书证,重在溯源。这是我国现代第一部较大规模的语文词书” 。而新《辞源》则“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增补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并删去少数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目”
。而新《辞源》则“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增补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并删去少数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目” 。其将兼收语文、百科的旧《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在释义原则上则遵从旧《辞源》的“由源以竟委”原则,“释义力求简明确切,并注意词语的来源和语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
。其将兼收语文、百科的旧《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在释义原则上则遵从旧《辞源》的“由源以竟委”原则,“释义力求简明确切,并注意词语的来源和语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 。而且,新《辞源》不仅注意单字释义的溯源问题,在复音词释义的探源方面也同样下了功夫。
。而且,新《辞源》不仅注意单字释义的溯源问题,在复音词释义的探源方面也同样下了功夫。
《辞源》的两个特点——“以常见为主”和“由源以竟委”,能够满足本论文写作时的语料要求。因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能够从先秦传承到现代汉语,多数必是常见的。另外,《辞源》在“由源以竟委”时对首见时代的探求又可以保障我们选取语料的可操作性和充分性。
在现代汉语复合词的选取方面,我们以《现汉》(第5版)作为语料的来源。《现汉》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全书收词约65000条,基本上反映了目前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 因此,本书以此作为现代汉语双音词语料是最为合适的。
因此,本书以此作为现代汉语双音词语料是最为合适的。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先秦传承复合词。这决定了我们选择语料要同时符合“先秦”“传承”“复合”三个标准,我们采用具体步骤如下:
1.语料的初步确定
初步语料的选定依据《辞源》及《现汉》的对比而来,第一步工作是把《辞源》中首见义是先秦并在《现汉》中存在的词条对照出来。所得到的词条总目为3026条。
2.叠音词和联绵词的排除
在判断联绵词时,采用学界普遍应用的两条标准:一是两个音节一旦拆开来,就不能各自表达完整的意义;二是词义不能看作第一个音节和第二个音节的组合意义。
从训释来看,古代注释家对联绵词的处理也常常作整体解释,正如王念孙所云:“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 如:
如:
参差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周南·关雎》)朱熹集传:“参差,长短不齐之貌。”
匍匐
嫂蛇行匍匐。(《战国策·秦策》)鲍彪注:“匍匐,伏地也。”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诗·大雅·生民》)朱熹集传:“匍匐,手足并行也。”
侘傺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楚辞·离骚》)王逸注:“侘傺,失志貌。”
由于联绵词来源的复杂性,同一个词放到汉语不同时期的语言系统中考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联绵词的产生大约有三个渠道:义合式、衍音式和摹声式。 后两类联绵词在成词之初,内部成分就具有不可分解性;“义合式”则不同,它在成词之初,内部的两个音节是各自有意义的单位,但由于长期连用以及语言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才凝固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部分词在结合的早期很难说是严格的联绵词。如:
后两类联绵词在成词之初,内部成分就具有不可分解性;“义合式”则不同,它在成词之初,内部的两个音节是各自有意义的单位,但由于长期连用以及语言中其他因素的影响才凝固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部分词在结合的早期很难说是严格的联绵词。如:
惆怅
在先秦文献中,“惆”“怅”和“惆怅”均可以单独使用表示“失意的样子”。
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荀子·礼论》)杨倞注:“惆然,怅然也。”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楚辞·九歌·山鬼》)
发展到现代汉语,“怅”还可以组成其他的词,如“怅然”“怅惘”等,但是“惆”如果离开这个词,则只是一个音节,没有实际的意义。
滂沱
在先秦文献中,“滂”“沱”可以单独使用,表示的意义和“水大”相关。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诗·召南·江有汜》)高亨注:“小水入于大水叫做沱。”
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宋玉《高唐赋》)
而且,“滂”单独使用还可以泛指“广大”。如:
滂心绰态,姣丽施只。(《楚辞·大招》)王逸注:“言美女心意广大,宽能容众,多姿绰态,调戏不穷。”
发展到现代汉语,“滂”“沱”都不再独立运用,而且“沱”除用于地名外,作为单独音节已不再表达实际意义。
本书确立的研究对象为“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这决定我们的判断是在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中来进行观察。因此,对于“义合式”形成的联绵词,也不能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经过离析,共有联绵词60个,叠音词96个。
3.字形上的离析和辨别
判断两个古今语言单位是否具有意义上的传承关系时,首先要对记录词语的字形进行辨别。由于汉字的字形以及记录职能的分化和转移,常会造成在古今汉语中用不同的字来记录同一个词(语素)的现象。例如:
侥幸
在先秦文献中,“侥幸”又可作“徼倖”“徼幸”“儌幸”“侥倖”。例如:
人实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国语·晋语》)
以险徼幸者,其求无餍。(《左传·哀公十六年》)
此以人之国侥幸也。(《庄子·在宥》)
《经义述闻·礼记上·不饶富》:“李善注《陈情表》引《礼记》‘小人行险以侥幸’云:‘侥与徼同。’今《中庸》作‘徼幸’。”《庄子·在宥》:“此以人之国侥幸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侥,字或作徼。”《玄应音义》卷三“侥倖”注:“侥,又作憿、徼二形。”可见,“徼倖”“徼幸”“儌幸”“侥倖”都是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现汉》中也有“侥幸”和“徼幸”两个词条,其中“徼幸”下注释为“见685页[侥幸]”。
再如古汉语中的“睿知”和现汉中“睿智”实为一词,“知”与“智”为同源分化字。类似的如“姻娅”与“姻亚”, “四肢”与“四支”, “边陲”与“边垂”, “微词”与“微辞”等。这些词之间尽管字形有异,但均可以确定为同一个词。
4.同形语言单位传承关系的确定
上面讨论的是异形同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为同形异构。语言的发展中,共时和历时层面,同形异构的语言单位都是存在的。共时层面主要是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划分;历时层面则是不同时代的同形结构是否具有传承关系的确定。鉴别一个现代汉语复合词是否和先秦同形语言单位之间具有传承关系,主要看两个语言单位整体意义是否具有关联性和可解释性,即能否在两个语言单位之间找到语义变化的可能途径。具体分作两步来考虑:首先看语言单位的整体意义、语素义以及语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对应性,如果有很紧密的对应性则一般具有传承关系;其次,对于无对应关系的词,再看两个语言单位能否找到意义衍生的节点,如果有则具有传承关系,没有则不具有传承关系。如:
失主
先秦意义为“失败的君主”。如:
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若失主不然,轻与人政而重予人马,轻予人军而重与人玉。(《管子·霸言》)
现代意义为“失落或失窃的财物的所有者”。两个“失主”中,“失”与“主”在意义上均无法对应。第一个“失”为“失败”义,第二个为“失窃、丢失”义;第一个“主”为“君主”义,第二个“主”为“主人”义。词义的发展也无法找到衍生的途径,只能看作偶然的同形。
名师
先秦意义为“精锐的部队”。如:
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韩非子·初见秦》)
现代意义为“有名的老师”。语素的意义无法对应,两个“师”,一个指“军队”,一个指“老师”。很明显,两个词不具有传承关系。
牧民
先秦意义为“统治百姓”。例如:
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国语·鲁语》)
现代意义为“牧区中以畜牧为主要职业的人”。前者两个语素之间的关系是动宾结构,后者则是偏正结构。不具有传承关系。
一般情况下,具有衍生关系的两个语言单位,其内部的语素义以及两个语素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有一些因词义变化而重新分析的词会出现例外,但这种现象很少,下文会有所论及)。因此,有些同形式的语言单位单纯从整体意义看似乎也能看到关联,但如果仔细分析其内部的语素意义以及语素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判断两个结构之间传承关系的牵强。如:
力作
尽力劳作。《韩非子·六反》:“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辞源》)
精心完成的功力深厚的作品。(《现汉》)
如果只看两个词义,前者为“尽力劳作”,后者为“尽力劳作的结果”。这种引申似乎也可解释得通。但是,当我们对这两个语言单位的内部语素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问题。前者“力”指“尽力”,后者“力”指的是“有功力的”;前者中的“作”指“劳作”,后者“作”指“作品”。前者为状中关系的修饰,后者为定中关系的修饰。因此,我们认为从内部语义构成和结构上说两者不具有传承关系。
还有一些双音结构,它们在先秦文献中可以构成两个不同结构类型的短语,就需要我们首先去辨明先秦时期的两个结构是否有衍生关系,其次要判断现代汉语中词的确定来源。如:
树木
既可以是动宾关系,表示“种植树木”。如: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
故欲致鱼者先通谷,欲来鸟者先树木。(《文子·上德》)
也可以为名词性的并列结构,表示“木本植物的总称”。如:
﹝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礼记·月令》)
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墨子·非攻下》)
两种结构的产生在于“树”在先秦文献中,既可以表示“种植”,又可以作为“木”的同义词使用。丁喜霞(2006)认为“‘树’的名词义在文献中的用例,早于‘树木’连用的时间,‘树木’同义并列表示‘木本植物的统称’的用例,在文献中也不晚于‘树木’用作动宾短语的用例” ,并由此得出“树木”的名词义项与动宾短语的“树木”不具有衍生关系。因此,我们只能把并列结构的“树木”看作传承复合词的源头。
,并由此得出“树木”的名词义项与动宾短语的“树木”不具有衍生关系。因此,我们只能把并列结构的“树木”看作传承复合词的源头。
另外,也有一些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多个意义,也需要我们判断这些意义之间是否都和先秦的同形结构之间具有传承关系。如:
陈言
《现汉》中设两个义项:①陈腐的语言。②陈述言辞。
在先秦文献中,“陈言”只有“陈述言辞”的义项。如:
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韩非子·备内》)
儒有澡身浴德,陈言而伏,静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孔子家语·儒行解》)
从现汉两个意义来对应,只有义项②来源于先秦,义项①和先秦的“陈言”不具有传承关系。
而有些语言单位尽管整体意义差别较大,但可以从源头上找到两者之间变化的节点,也应视为衍生关系。如:
万福
在先秦文献中的意义为“多福”,常用作祝祷之词。
和鸾雝雝,万福攸同。(《诗·小雅·蓼萧》)
由于古代妇女相见行礼,常口称万福,因此,表示“旧时妇女行的敬礼,两手松松抱拳重叠在胸前右下侧上下移动,同时略做鞠躬的姿势”也称为“万福”。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把两个“万福”钩稽起来,它们之间具有传承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共离析出252个与先秦同形结构不具有衍生关系的现代汉语复合词,这部分词将排除在本书的研究对象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词在先秦文献中就已经是只有语法意义的虚词,无法将其视为复合词,如“而已”“於乎”“於戏”,这些词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根据以上原则和方法的处理,共得出具有衍生关系的先秦传承复合词词条261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