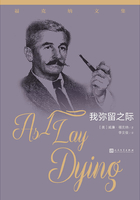
前言
——“他们在苦熬”
这是怎么样的一部书呢?说它是悲剧吧,不大像,说它是喜剧,也不合适。面对着书中的一出出场景,我们刚想笑,马上有别一样的感情涌上心头;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真的用得上“啼笑皆非”这样一句中国成语了。难怪国外的批评家说这是一出悲喜剧。其实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荒诞剧,因为它具有五十年代荒诞剧的一切特色,虽然在它出版的1930年,世界文坛上还没有荒诞剧这个名称。
《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如果与福克纳同时期创作的另一本小说《圣殿》(Sanctuary,1931)并读,主旨就显得更清楚了。(《圣殿》的出版在《我弥留之际》之后,其实写成却在《我弥留之际》之前。)在《圣殿》里,福克纳写出了社会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人心的丑恶,写出了“恶”的普遍存在。而在《我弥留之际》里,福克纳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丑陋的美国人”。
《我弥留之际》写的是发生在十天之内的事。小说开始时,艾迪·本德仑躺在病榻上。这个小学教员出身的农妇在受了几十年的熬煎后,终将撒手归天。窗外是晦暗的黄昏,大儿子卡什在给她赶制棺材。艾迪曾取得丈夫的口头保证,在她死后,遗体一定要运到她娘家人的墓地去安葬。在三天的准备、等待与大殓之后,到四十英里外的杰弗生去的一次“苦难的历程”开始了。一路上,经过了种种磨难,大水差点冲走了棺材,大火几乎把遗体焚化,越来越重的尸臭招来了众多的秃鹰,疲惫不堪的一家人终于来到目的地,安葬了艾迪。在这个过程中,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了,卡什失去了一条腿,老二达尔进了疯人院,三儿朱厄尔失去了他心爱的马,女儿杜威·德尔没有打成胎,小儿子瓦达曼没有得到他向往的小火车,而作为一家之主的安斯·本德仑却配上了假牙,娶回了一位新的太太……
《我弥留之际》写的是一次历险,就这一点来说,它有点像《奥德修记》[1],但是它完全没有《奥德修记》的英雄色彩。它在框架上又有点像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2]。在风格上,它更像《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也是让人笑的时候带着泪的一本书。(福克纳说《堂吉诃德》他“年年都要看,就像有些人读《圣经》那样”。)但是《我弥留之际》毕竟是一部现代小说,用欣赏《堂吉诃德》的眼光来看待它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三十年代时,美国的一些批评家曾把《我弥留之际》作为一本现实主义小说来分析,把它看成关于美国南方穷苦白人农民的一部风俗志,一篇社会调查。用那样的眼光来看《我弥留之际》更是没有对准焦距。这非但无助于领会作品的主旨,反而会导致得出“歪曲贫农形象”这样的结论。
那么,应该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我弥留之际》呢?
迈克尔·米尔盖特在他的《威廉·福克纳的成就》这本书里说:“福克纳的主要目的更像是迫使读者以比书中的人物与行动第一眼看去所需要或值得的更高一层、更有普遍意义的角度来读这本小说,来理解本德仑一家及其历险记。还有,尽管这个故事读来让人不愉快,它经常具有一种阴阴惨惨的狂想曲的气氛,但是它使我们逐渐领会,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human en-durance)的一个原始的寓言,是整个人类经验的一幅悲喜剧式的图景。”美国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也在他的《威廉·福克纳浅介》一书里说:“要考察福克纳如何利用有限的、乡土的材料来刻画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更有用的方法也许是把《我弥留之际》当作一首牧歌来读。首先,我们必须把说到牧歌就必得有牧童们在美妙无比的世外桃源里唱歌跳舞这样的观念排除出去。所谓牧歌——我这里借用了威廉·燕卜荪的概念——是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特别是深谙世故的读者的世界。这样的(有普遍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此,牧歌的模式便成为一个表现带普遍性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在表现时既可以有新鲜的洞察力,也可以与问题保持适当的美学距离。”布鲁克斯继续写道:“更具体地说,大车里所运载的本德仑一家其实是我们这个复杂得多的社会的有代表意义的缩影。这里存在着生活中一些有永恒意义的问题。例如:终止了受挫的一生的死亡、兄弟阋墙、驱使我们走向不同目标的五花八门的动机、庄严地承担下来的诺言的后果、家族的骄傲、家庭的忠诚与背叛、荣誉,以及英雄行为的实质。”[3]
米尔盖特和布鲁克斯的意思很清楚:应该把《我弥留之际》作为寓言来读,不应那么实、那么死地把本德仑一家视为美国南方穷苦农民的“现实主义形象”,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全人类的象征,他们的弱点与缺点是普通人身上存在的弱点与缺点,他们的状态也是人类的普遍状态。福克纳对人类状况的概括是否准确,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弥留之际》不能作为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来读,这一点,时至今日,恐怕不应再有异议了。
布鲁克斯列举了一连串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弥留之际》中的确都有所涉及。但是,什么问题是作者最为关注的呢?他所着重表现的是人类行为的哪一种状态呢?他要揭示给读者的是什么样的寓意呢?
读过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人也许会注意到,该书的结尾是这样一个只有主语和谓语、没有任何修饰成分的简单句:“他们在苦熬”(They endured)。从字面上看,这是对迪尔西及其黑人同胞的写照,但何尝不可以理解为对全人类命运的概括描述。在福克纳看来,人类存在虽然已有千百万年的历史,但是时时刻刻仍然在为自身的生存殚精竭虑,流血流汗,说他们“在苦熬”一点儿也不过分。在多读了一些福克纳的作品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想法并非福克纳灵魂里的一闪念,他像是抑制不住经常要回到这个主题上来。“endure”与以名词形式出现的“endurance”多次在福克纳的笔底下出现。在著名的中篇小说《熊》(1942)里,他说黑人“会挺过去的”(will endure)[4]。他的诺贝尔奖演说词只有短短的四小段,“endure”或“endurance”却出现了五次之多。而且福克纳仿佛有意要让读者铭记在心似的,这个词还出现在演说词最后一个带格言意味的句子里:“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类的记录,它可以作为一个支柱,一根栋梁,帮助人类渡过难关(endure),蓬勃发展。”四年之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寓言》(1954)里,福克纳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类和他的愚蠢行为会继续存在下去(will endure)和蓬勃发展。”[5]——当然不仅仅是文字,而且也是中心思想。1955年,他在答记者问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虽然换了一个说法。他说:“我也很想写一本乔治·奥威尔的《1984》那样的书,它可以证明我一直在鼓吹的思想:人是不可摧毁的(man is indestructible),因为他有争取自由的单纯思想。”[6]
以上众多的例子足以证明,对于人类忍受苦难的能力,以及终将战胜苦难[7]这样的思想,福克纳是一直在考虑与关注的。国外的批评家似乎还没有人专门撰文探讨福克纳用字遣词上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但是他们对于福克纳如此执着地关心着这个命题是注意到了的。法国作家加缪指出:“梅尔维尔之后,还没有一个美国作家像福克纳那样写到受苦。”[8]法国批评家克洛德-埃德蒙·马涅认为:“福克纳作品中的人的状况颇似《旧约》中所刻画的人类状况:人在自己亦难以阐明的历史中极其痛苦地摸索前进。”[9]克林斯·布鲁克斯干脆用总结的口吻概括说:“福克纳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一直关注着人类的忍受能力,他们能面对何等样的考验,他们能完成什么样的业绩。本德仑一家如何设法安葬艾迪·本德仑的故事为福克纳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类受苦与行动能力的极其优越的角度。这次英勇的历险牵涉到多种多样的动机与多种多样的反应。”[10]
这些外国作家、批评家的论断应该说是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在做了以上的考察之后,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福克纳是一位关注人类的苦难命运,竭诚希望与热情地鼓励他们战胜困难、走向美好的未来的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至于他为什么有时候把受苦的人们写得这么丑陋,这个问题将放在后面适当的场合阐述。现在,先让我们对《我弥留之际》的主要人物做些分析,以此说明福克纳在这部小说里是怎样表现他的关于人,关于人的苦难与奋斗的思想的。
女性在福克纳的作品中一向占着相当重的分量。小说里弥留中的“我”——艾迪·本德仑,显然处于一个轴心的位置。这个家庭的主妇首先就是个被生活挫败的人。她年轻时受到父亲悲观思想的影响。父亲常对她说:“活着的理由就是为长期的死做好准备。”她当过小学教员,但是她既不爱自己的职业,也不爱她的学生。她是一个孤儿,也许是因为害怕孤独,嫁给了也是孤儿的安斯。婚后不久,在她心中,安斯已经死了。结婚之后,她感情上也起过一次波澜,但是她的情人惠特菲尔德牧师和《红字》里的狄姆斯台尔一样,也是个懦夫。受骗上当使她不再相信“言语”的真实性。在贫穷与孤独中操劳了一辈子之后,艾迪终于死去。也许是因为除了她娘家的血亲关系之外,对别的都感到不可靠,她要求和娘家人埋葬在一起。小说中只有一段独白属于她,这一节(第40节[11])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出现,那时她已经死去好几天。读这段文字有如深夜听一个怨魂在喁喁泣诉。可以这样说,艾迪·本德仑直到死去也始终没有处理好与生活的关系。她的一生本身就是一次“苦难的历程”。
艾迪的大儿子卡什是个只知闷头干活的老实人。他是个好木匠,对他来说,为母亲及时做好棺材就是最后一次表达对母亲的爱。因此,他就在她窗外赶制,做好一点就拿给她看,这是他的劳动成果,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忌讳的。他迂得可笑,也迂得可爱。福克纳所写他对于棺材制作的十三条设想(第18节[12])固然有些夸张,但还是刻画出了把技艺看得高于一切的手艺人的灵魂。卡什木讷寡语,很能吃苦。就能忍受痛苦与乐于自我牺牲来说,他是福克纳所赞美的受苦精神的集中体现。为这次出殡他失去了一条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背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影子。和耶稣一样,他也是一个木匠。这一点也许不仅仅是偶合。
达尔的形象比较复杂。他属于西方文学里那种“疯子—先知”的典型。在全书的五十九节中,有十九节是由他来叙述的。在这支内心独白者组成的“球队”中,他像是起着一个“二传手”的作用。许多线索像球那样传给了他,又由他再传出去,故事也因此得以展开。从这一点说,他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家本人的作用。他总是在分析、评论他周围的人物。他的观察力、思考力特别强,甚至达到具有“特异功能”的程度。唯其因为能看透别人的隐私,他才受到来自各方的冷眼与憎厌。他反对把母亲已经腐烂的尸体运到远处去安葬的主张应该说是合乎理性的,但是他采取了纵火的办法来贯彻这一主张,结果授人以口实,被送进了疯人院。世界上不少失败者都和达尔有着同样的命运。达尔是一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畸零人”,他最具有现代文学中“现代人”形象的特点。布鲁克斯说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和半个存在主义者”[13]。这样的人总是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几乎都集中于自己的一身。
朱厄尔爱马。书中把他和马的关系写得十分出色,使人想起朱厄尔就会同时想起他的马。他们密切不可分,几乎成了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centaur)。为了得到这匹马,他曾付出极大的代价。他脾气激烈暴躁,像一匹烈马。他生性骄傲,像一匹高贵的名马。但是从水里救出母亲遗体的是他,从火里扛出棺材的也是他。他又像一匹忠心耿耿的良驹。但是正如千里马不能适应车舆犁耙的役使一样,朱厄尔在闭塞落后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肯定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杜威·德尔具有福克纳笔下经常出现的“原始人”的气质。书中写了一大段她与牛“感情交流”的过程,决不是偶然的。母牛乳房胀疼,希望她来缓解。她心里有难言之隐,只能向不会说话的母牛倾诉。这二者之间原本没有太大的差别。她为了设法堕胎,一再催促父亲进城,结果不但目的没有达到,还吃了哑巴亏。她没有自卫能力,却可以加害于人。是她,告发了达尔的纵火行为,揪住他让疯人院的工作人员得以从容行动。她既懦弱却又凶残,也许这就是福克纳所说的“人类的愚蠢行为”吧。不管怎么说,除了回到乡间,生下私生子,度过比母亲还不如的受苦人的一生之外,她是不会有更好的命运的。
小儿子瓦达曼是个弱智儿童,其智商比《喧哗与骚动》里的班吉稍高,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否则他就不会演出下面这一幕幕了:把母亲与大鱼混淆起来,认为皮保迪大夫是母亲的谋杀者,打走了他的马,在棺材盖上钻眼毁损了母亲的遗容……就和他进城一次得不到梦寐以求的玩具小火车一样,在新的本德仑太太的统治下,他也决不会实现他别的渺小的希望的。
我们把一家之主的安斯·本德仑放在最后来说,是因为他身上可鄙、丑恶的成分比其他人都多。克林斯·布鲁克斯说:“安斯肯定是福克纳创造出来的人物中最最可鄙的一个。”[14]世界上丑恶现象之多与突出常令人难以解释,使得许多思想家与作家不得不从“人性恶”上面去找原因。马克·吐温晚年就对人类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他说:“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丑恶的。在世间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最凶残——这是一切本能、情欲和恶习中最下流、最卑鄙的品质。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痛苦的生物,他并非出于什么目的,而只是意识到他能够制造它而已。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才具有卑鄙下流的才智。”福克纳没有马克·吐温走得那么远,但他也在作品中——特别是早期的作品中——写到了“人类的愚蠢行为”如何毁灭了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东西。在《我弥留之际》中,安斯·本德仑的懒惰与自私就没能把妻子从原有的悲观厌世情绪中摆脱出来,使她过了毫无光彩的一生,终于在郁郁不欢中死去。他不断地剥夺子女的权益,使他们也成为狭隘、自私的人,使他们在感情上互相难以沟通,甚至于彼此仇视。自我净化是人类走向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福克纳才在他的作品中突出了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南方人性格中丑陋的一面。1955年福克纳访问日本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把人写得那么卑劣。福克纳回答说:“我认为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太爱我的国家了,所以想纠正它的错误。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我的职业范围之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羞辱美国,批评美国,设法显示它的邪恶与善良之间的差别,它卑劣的时刻与诚实、正直、自豪的时刻之间的差别,去提醒宽容邪恶的人们,美国也有过光辉灿烂的时刻,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作为一个民族,也曾创造过光辉、美好的事迹,仅仅写美国的善良对于改变它的邪恶是无补于事的。我必须把邪恶的方面告诉人民,使他们非常愤怒,非常羞愧,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去改变那些邪恶的东西。”[15]看来,福克纳写本德仑一家,与鲁迅写阿Q是有共同之处的(且不说这两篇作品都具有寓言的特点)。他对美国南方的农民,也有着鲁迅对中国人民那样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他写自己同胞“国民性”中低劣的一面,还是为了使美国人振奋自强。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不赞同他这样做。何况他在写这些方面的同时,仍然写出了他们勇敢、自我牺牲与理性的一面,如朱厄尔、卡什与达尔的那些表现。
而且在总体上,福克纳还是把这次出殡作为一个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行为来歌颂的。尽管有种种愚蠢、自私、野蛮的表现,这一家人还是为了信守诺言,尊重亲人感情,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与阻碍,完成了他们的一项使命。福克纳自己说:“《我弥留之际》一书中的本德仑一家,也是和自己的命运极力搏斗的。”[16]可以认为,《我弥留之际》是写一群人的一次“奥德赛”,一群有着各种精神创伤的普通人的一次充满痛苦与磨难的“奥德赛”。从人类总的状况来看,人类仍然是在盲目、无知的状态之中摸索着走向进步与光明。每走一步,他们都要犯下一些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就这个意义说,本德仑一家不失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加缪对福克纳作品的主题所作的概括也许是绝对化了一些,但是并不是没有道理。他说:“福克纳给予我们一个古老然而也永远是现代的主题。这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悲剧:盲人在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福克纳有他自己的概括方式,他说:“到处都同样是一场不知道通往何处的越野赛跑。”[17]在三十年代福克纳所在的世界里,这样的描述不失为准确与真实。福克纳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了这样的现象,应该说是忠实地反映了他周围的现实。
李文俊
[1] 据出版福克纳作品的“兰登书屋”的编辑萨克斯·康敏斯说,《我弥留之际》这个题目引自威廉·马礼斯1925年出版的《奥德修记》的英译。在《奥德修记》里,躺着等死的“我”是阿伽门农,他是被妻子及其情夫杀害的。就妻子与人私通这一点来说,阿伽门农的故事与《我弥留之际》有共通之处。(见麦克斯·普泽尔:《地域的天才》,198—199页,207页,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85年。)
[2] 英国批评家迈克尔·米尔盖特特别强调这一点,他甚至认为“本德仑”(Bundred)这个姓与《天路历程》中基督徒身上的负担(burden)有一定的关系,这一家人进行的是一次具有冷嘲意味的朝圣者的历程。杰弗生镇可以比拟为“天堂”,安斯得到了他的“报酬”:假牙、新妻与留声机。达尔却在天堂的门前走上了一条通向地狱的路。(见迈克尔·米尔盖特:《威廉·福克纳的成就》,110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78年。)
[3] 克林斯·布鲁克斯:《威廉·福克纳浅介》,88—89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年。
[4] 见《去吧,摩西》294页,“酒库丛书”,1973年。
[5] 《寓言》,354页,兰登书屋版,1954年。
[6] 《园中之狮》,241页,“野牛丛书”,1980年。文中排黑体字处为本文作者所改。
[7] 在英语里,“endure”一词兼有“忍受”(to bear)与“挺过来”(to last)这两层意思。见《牛津大词典》。
[8] 《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1960年2月21日。
[9] 《福克纳评论集》,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0] 《威廉·福克纳浅介》,94页。
[11] 见本书第144页。
[12] 见本书第68—69页。
[13] 《威廉·福克纳浅介》,87页。
[14] 《威廉·福克纳浅介》,82页。
[15] 《园中之狮》,159—160页。
[16] 《福克纳评论集》,273页。
[17] 同上,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