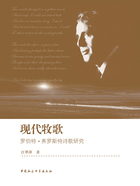
序
美国现代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在英美诗歌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弗罗斯特浸润于西方古典文学传统,同时也深受美国超验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并以自己异乎寻常的个性气质与源远流长的西方传统审美资源和英美哲学的近代流派互动,予以融合创新,形成了别致超绝的弗罗斯特风格。自16岁开始写诗直到89岁去世,在半个多世纪里弗罗斯特笔耕不辍,以其独特的诗歌艺术和丰硕的创作成果引起了国内外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但是弗罗斯特曾被烙上传统诗人、自然诗人和新英格兰农民诗人的印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弗罗斯特在中国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也是中国较少出现系统的弗罗斯特研究专著的原因。汪翠萍博士的专著《现代牧歌: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研究》作为目前中国大陆尚不多见的专门以弗罗斯特为研究对象的中文著作,或许能抛砖引玉,为国内相对落后的弗罗斯特研究的综合与深化作出一些开拓性和铺垫性的工作。
汪翠萍博士在纵观国内外弗罗斯特诗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和尚有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发现了弗罗斯特与众不同的创作视野和文学想象力,从中提炼出“牧歌”这一视角,借以研究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作。她在这部专著里结合西方牧歌传统、美国思想史以及弗罗斯特个人特殊的社会文化经历,精辟地指出,弗罗斯特以“乡野之人”的身份描写农村,以远离尘嚣的自然界为大众读者提供一种乐园图示。这一典型形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在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困扰之下的美国文学给予读者的印象。弗罗斯特着力描写新英格兰宁静的乡村景物和平凡的日常生活,以富于想象的方式建构了新英格兰乡村中的真善美,这似乎与严酷的现实格格不入。但是弗罗斯特也看到自然界并不完全是秀丽的景色,其背后隐藏着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他的诗歌流露出人类对自然界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笔下,自然界既富于魅力也潜藏着危险,既具有璀璨的景象又具有毁灭的力量。因而他笔下的乡野世界并非人类社会永恒的避难所,诗人在渲染西方文学传统中质朴清纯的牧歌情调的同时,也不加回避地描写乡野世界里存在的黑暗与罪恶。这足以表明诗人并没有一味神往与世隔绝的古希腊阿卡迪亚,而是头脑清醒地正视当代社会的严酷现实。
就具体的诗歌创作而言,弗罗斯特扬弃西方自启蒙主义时代以来一直曲高和寡的精英话语,而怀着众生平等的意识参与社会批评话语的建构,以清新简约的形式和切近读者的内容赋予人生诗意的启迪。弗罗斯特拆解了西方传统的阿卡迪亚世界,对牧歌文学作出了新的发展:他的牧歌不是引导读者走向自然当中的陶然乐土和童年岁月的纯真世界,而是启示人们冷静客观地正视现代文明和成年时代的理智世界,使之在喧嚣和纷繁当中克服现实的混乱,在世俗痛苦当中达到灵魂的安宁。汪翠萍博士的这本专著将牧歌的特质概括为传统性、乡土性、现实性和大众性等方面内容,以此将弗罗斯特各个时期的诗歌有机地融合起来,通过深入的分析,得出弗罗斯特是一位现代的牧歌诗人这一结论,此种见解独到,颇具说服力。
该书将弗罗斯特看似简单直白、平淡不惊的诗作放到西方牧歌传统中予以审视,聚焦于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从内涵和外延不断被扩展的牧歌概念和弗罗斯特诗歌与牧歌的联系出发,揭示弗罗斯特的诗歌是西方牧歌这一整体形式中的一部分,并且指出读者只有立足于牧歌这一传统的文学样式才能全面而客观地发掘弗罗斯特诗歌当中蕴涵的深意;第二,结合阿卡迪亚与新英格兰地域的相似性,阐述弗罗斯特笔下的新英格兰地域所潜藏的文化内涵;第三,通过现代美国与维吉尔牧歌中的黄金时代的内在联系,论述弗罗斯特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关注及其对人类理想社会“黄金时代”的期待;第四,分析弗罗斯特诗歌语言的特色并结合弗罗斯特的人生经历和时代环境等因素,探究弗罗斯特与主流现代派诗人相比的独特价值所在,以及诗人对传统牧歌的超越与发展。汪翠萍博士的专著在这几方面的论证深入透辟,充满独抒性灵的发现和不拘格调的洞见,十分有效地拓宽了弗罗斯特诗歌作品中的乡野景观在现代世界当中的深层意义。
该书并不囿于用新批评的方法从事文本的内部研究,而是结合中西方诸多研究成果,联系弗罗斯特的作品、他的人生历程及其所处时代和文学背景,综合考察弗罗斯特运用牧歌模式的缘由、表现以及他在牧歌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建树。在分析弗罗斯特诗歌时,汪翠萍博士有意识地在弗罗斯特诗作与相关艺术作品的比较当中,按照牧歌文学的标准对其作出批评,同时结合有关的历史事件和现实事例,挖掘弗罗斯特诗作中的意义和内涵。阿兰·布鲁姆指出,诗歌所面向的对象往往涉及作为整体的知识。该书的建构符合诗歌的这一特点,也运用一种宏观的总体研究方式,以弗罗斯特的诗集、书信、传记、讲稿、随笔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对诗人运用的牧歌模式作出历时的概览和共时的分析,进而对弗罗斯特诗歌作出了完整而客观的认识。在具体研究中,汪翠萍博士采用分析批评的方法,尤其是在阅读弗罗斯特原作的前提下,从弗罗斯特运用牧歌模式的文化语境以及牧歌主题、意义等诸多层面进行论证,并结合现当代批评理论中的相关论述来充实这部专著中的观点。在这些方面该书有的放矢,颇具敦实醇厚的学术价值。
弗罗斯特既有大量描写乡村景物和农耕生活场景的诗歌,又有针砭时弊、嘲讽纤巧的作品。他的诗歌雅俗共赏,内涵深邃,在受到世界各地读者广泛赞誉的同时,也有批评家不肯将其纳入文学的尊贵殿堂。诚如汪翠萍博士指出的,弗罗斯特卓尔不群的人生道路和特立独行的诗歌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批评家对他及其作品产生误读和曲解,由此引发对他的诗歌言过其实的褒扬或带有偏见的贬低,导致他在批评视野中的形象若隐若现,难以聚焦。对于这样一位颇受争议的诗人,虽然有着充分的空间可供拓展探索深度和广度,但是在学界有不少方面尚无定论,在相关研究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弗罗斯特的创作思想和诗歌内涵诚非易事。“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南朝宋文学家刘季伯此语不仅与别具一格的弗罗斯特诗歌创作本身恰好相符,也适用于像这部专著一样独辟蹊径的弗罗斯特诗歌研究。希望汪翠萍博士克服难点,进一步深入探析弗罗斯特的诗歌创作,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不断探索,争取达到更高的学术造诣。
孙宏
2016年12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