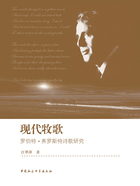
绪论 备受争议的罗伯特·弗罗斯特
1961年1月20日,在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年届87岁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声音洪亮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一无保留的奉献》(“The Gift Outright”)。这位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贫穷诗人,历经少年时期初试锋芒的失败,成名后遭到无数评论家的误解甚至批判,却矢志不渝,苦苦奋斗,终于在这一天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罗伯特·弗罗斯特大器晚成,在他38岁之前,这位自幼在母亲的引导下熟读《圣经》、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英美传统诗歌的诗人,除了在美国几家杂志上发表过诗歌以及自己印制的薄薄两本小册子《曙光》(Twilight)之外,还没有公开出版过任何著作。1912年,弗罗斯特怀揣诗歌文稿以及致力于诗歌创作的梦想从美国来到英国伦敦。弗罗斯特命运的转折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发生在1913年2月8日晚上。这一天,弗罗斯特参加了哈罗德·门罗(Harold Edward Monroe)在伦敦德文郡街(Devonshire Street)的诗歌书店揭幕典礼,并在这晚的聚会上遇见英国文学主流社会里几位声名显赫的诗人。弗罗斯特受到弗兰克·弗林特(Frank Flint)的注意,被告知他应该去见见他的同胞,当时已在英国享有盛名的美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此后的一个多月,弗罗斯特前去拜访庞德。在庞德的帮助之下,弗罗斯特很快被英国文学界接受,当时英国的相关报刊纷纷刊登评论文章,称赞弗罗斯特的诗歌给英国人带来一种真挚、坦率、淳朴之风,英国评论家的热情赞扬又随即引起美国出版界的重视。1913年,弗罗斯特终于幸运地在异域他乡步入英美文坛,而1913年在文学艺术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正如彼得·沃森所评论的:“历史在每一个阶段上常给人以时间来品味那永久凸显的、真正确定性的转折点。1913年乃是这种转折点。”[1]1913年,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艺术展“军械库展览会”(The Armory Show)[2]在纽约举行,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等现代艺术走进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物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学和绘画等领域的理论视野熔为一炉。面对一个技术爆炸的影响无远弗届的崭新世界,在这种传统与现代交锋的时刻,弗罗斯特发表了《少年的心愿》(A Boy's Will,1913),以明白晓畅的句子,传统的诗歌形式,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描述新英格兰[3]地域。弗罗斯特的这部诗集奠定了他在评论家乃至读者大众心目中的基本形象,他常被称作“新英格兰的农民诗人”,是从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到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中转站,是“朗费罗之后最孚众望的美国诗人”。[4]这部诗集中的作品以其质朴而睿智的独特风格和宁静而秀丽的乡野景色受到人们与日俱增的青睐,也获得弗林特、庞德等重要评论家和诗人的好评。
此后,弗罗斯特的诗集纷至沓来。他的第二部叙事诗集《波士顿以北》(North of Boston,1914)以其简单明了而又寓意复杂的隽永风格使他一时之间立于英美文坛中的显著位置,成为与庞德、T.S.艾略特(T.S.Eliot)和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并列的“现代主义的开创者之一”。[5]这两部诗集确立了弗罗斯特这位诗坛新秀的地位,而与之相比,诗人回到美国后出版的第三部诗集《山间》(Mountain Interval,1916)却显得虎头蛇尾。尽管这部诗集包含了《一条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一个老人的冬夜》(“An Old Man's Winter Night”)、《白桦树》(“Birches”)和《熄灭吧,熄灭!》(“Out,Out—”)等为读者熟知的诗歌,但是连弗罗斯特本人也对这部诗集感到失望。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在《现代美国诗歌趋势》(Tendencies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1917)一书中认为弗罗斯特的第三部诗集并没有为诗人的成就增辉,路易斯·布谨(Louise Bogan)在《美国诗歌成就:1900—1950》(Achievement in American Poetry:1900-1950,1951)一书中回顾弗罗斯特的诗歌创作时甚至不予探讨这部诗集。就在评论家们预言弗罗斯特的诗歌创作将如昙花一现时,弗罗斯特出版了他的第四部诗集《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1923)。在这部诗集的作品中,弗罗斯特怀着对新英格兰的地域之情娴熟地运用当地口语,将叙述与抒情融为一体,获得评论家们众口一词的称赞。约翰·法拉(John Farrar)甚至认为:“这可能是弗罗斯特诗作中最完美的一部,是弗罗斯特收获的丰硕果实。”[6]这部诗集为诗人赢得1924年的普利策奖(Pulitzer Award),并以其感染力确立了诗人在美国文坛的地位。诗人弗罗斯特一生可谓多灾多难,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其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在人生沧桑和社会巨变当中,弗罗斯特坚定地把诗看成生命、人格和信念的最宝贵的一部分,执着地在诗歌创作中苦苦思索,恬静平和地审视着尘世生活。自16岁写诗一直到89岁去世,在半个多世纪里弗罗斯特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十几部作品,包括《西去的溪流》(West-Running Brook,1928)、《山外有山》(A Further Range,1936)、《见证树》(A Witness Tree,1942)、《绒毛绣线菊》(Steeple Bush,1947)和《在林间空地》(In the Clearing,1962)等诗集,以及《出路》(A Way Out:A One Act Play,1929)、《在一家艺术品制造厂》(In an Art Factory,1952)、《理智假面具》(A Masque of Reason,1945)和《仁慈假面具》(A Masque of Mercy,1947)等戏剧作品。这些诗作异彩纷呈,有朴素无华、寓意深刻的抒情短诗,戏剧性浓烈、艺术性高超的叙事长诗以及无韵诗体、变体十四行诗和双行体诗等各种体裁。
弗罗斯特的作品虽然形式多样,但他始终不肯追随自由诗体的潮流,而以个人的兴趣探索出汇集传统的抑扬格韵律和日常生活话语,古典人文情怀和现代怀疑精神的新诗体,将独特的形象、瞬间的境界、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哲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弗罗斯特对英美现代诗歌的独特贡献成就了美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他四次荣膺美国普利策奖(《新罕布什尔》《诗歌选集》《山外有山》《见证树》分别获得1924年、1931年、1937年和1943年的普利策奖),并获得包括牛津、剑桥在内的多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成为《时代》(Time)和《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人物,获得了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大小小各种荣誉称号。弗罗斯特也因其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在英美诗歌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曾将其与拉尔夫·爱默生、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艾米莉·狄金森、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等诗人并列,称之为“我们的大诗人”。[7]各国的评论家纷纷称其为“最伟大的诗人之一”[8],以其杰出的诗才形成与艾略特诗风迥然不同的现代美国诗歌的另一中心[9],是20世纪美国诗坛五巨擘之一。[10]弗罗斯特的艺术选择和丰硕的诗歌成就对英美诗人产生重要的影响。1987年美国文学史上第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其受奖词中向被诺贝尔文学奖错过而已逝世的现代杰出“幽灵”们致意,布罗茨基认为弗罗斯特以及曼德里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奥登比自己更适合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讲坛上,而他自己虽然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11]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将弗罗斯特视为自己的艺术宗师。2005年由依阿华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Iowa Press)出版的诗歌集《访问弗罗斯特:受到罗伯特·弗罗斯特生活和创作启迪的诗歌》(Visiting Frost:Poems Inspired by 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Frost,2005)则汇集了受到弗罗斯特影响的100位诗人创作的诗歌作品。不仅如此,弗罗斯特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赞誉。在他晚年时期,美国公众称其为“圣哲”,在他75岁生日之际,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向他祝寿,尊其为“民族诗人”。1958年至1959年,弗罗斯特受邀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被誉为非官方的“桂冠诗人”。1998年,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品斯基(Robert Pinsky)从18000份问卷调查中得知,罗伯特·弗罗斯特是当时美国诗坛“最受公众欢迎的诗人”。[12]弗罗斯特也日渐享有跨国的名声,于1952年作为代表之一参加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世界作家大会,于1957年作为友好使节重游英国,同时接受了牛津、剑桥和爱尔兰国立大学所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于1961年访问以色列、雅典和伦敦,于1962年作为白宫的友好使者访问苏联。
弗罗斯特日渐超越空间的限制,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在读者大众对弗罗斯特及其诗作热烈赞许的同时,以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为代表的批评家却不肯将弗罗斯特的诗歌纳入文学的尊贵殿堂。他们对弗罗斯特获得如此多的赞誉提出质问,认为他所获荣誉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味,他“经常被那些不喜欢诗歌的人过于热烈地称赞”。[13]以伊沃尔·温特斯(Yvor Winters)也相信弗罗斯特的诗作“既被过高地称赞又被错误地理解”。[14]温特斯主张应该联系当时的文学风气来合理地理解弗罗斯特的诗歌,认为美国的读者并不严肃地对待诗歌也并不喜爱严肃的诗歌,而弗罗斯特创作的乡村主题以及简单朴素的诗歌风格正好迎合美国读者的喜爱,这使得弗罗斯特拥有众多的读者。温特斯因此认为弗罗斯特可能被描述为一位好诗人,但绝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弗罗斯特成名后似乎好出风头,显然成为了一位名人、空谈家、公众人物和文化使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作为诗人的身份,使他遭到学术评论界的刻意贬低。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学术评论家们普遍欣赏庞德、艾略特和史蒂文斯等主流现代派诗人的艰深之作,讲究句子的碎片化、形式的不规则化和主题的跳跃化,而不那么看重弗罗斯特那些看似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田园诗。正如约翰·莱伦(John Lynen)所指出的:“弗罗斯特创作的诗歌与他同时代主要作家创作的诗歌截然不同……弗罗斯特的诗歌是明白晓畅的句子,传统的诗歌形式,接近日常生活的语言。诗歌中没有晦涩,没有拐弯抹角地提到但丁和启示录,没有深奥的知识或个人化密集的象征。”[15]由于这些诗歌特征,弗罗斯特作为一位诗人在主流现代派风起云涌的时代,也很难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理解。
弗罗斯特一方面久负盛名,另一方面又遭人质疑,人们众说纷纭。而弗罗斯特的文学生涯也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试想,一位新英格兰乡村的农民却集美国文学家所能获得的荣誉于一身,一位悲剧式的人物却始终在众人前面带着圣诞老人般的微笑安静地朗诵自己的诗作,一位现代诗人却始终不渝地坚守传统,选择一条未被别人选择的路。弗罗斯特卓尔不群的人生道路和诗歌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批评家对他及其作品产生误读和曲解,由此引发对他的诗歌言过其实的褒扬或带有偏见的贬低,导致他在批评视野中的形象或明或暗,难以定论。弗里德里希·席勒曾指出:“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维和意愿的主动状态的转移,只能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来完成。”[16]席勒认为感性的人不可能直接发展成为理性的人,必须首先变成审美的人,人在审美状态中得到净化提高,因而可以按照自由的法则从感性的人发展成为理性的人。有缘于此,在阅读弗罗斯特的诗歌作品时,需要现代读者遵从自由的法则,带着审美的愉悦,发现弗罗斯特在平凡中寻找诗意的态度,探索弗罗斯特在充满喧嚣的现代世界里化平乏为有趣、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从而以理性的思维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弗罗斯特诗歌,进而以诗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1]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2] 该绘画和雕塑展览会正式名称为国际现代艺术展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于1913年在纽约市第69兵团军械库举行。展览会的举办由美国画家与雕塑家协会构思,原本仅选择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参展,后来兼收了欧洲现代派作品。在展出的1300件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欧洲。此次展览会展出了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等艺术流派的作品,例如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ois Goyard)、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等艺术家的代表作品。
[3] 新英格兰是指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区域。该区域包括美国的六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麻省)。马萨诸塞州(麻省)首府波士顿是该区域最大的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新英格兰不仅拥有大批一脉相承的文学杰作,这可以上溯到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的《普利茅斯开发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而且还拥有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和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这样一批优秀作家,以及亨利·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弗罗斯特这样一批足以证明美国诗歌堪与英国诗歌相媲美的杰出诗人。
[4] 车成安主编:《外国文艺思潮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5] Nancy Lewis Tuten and John Zubizarreta eds.,The Robert Frost Encyclopedia,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2001,p.233.
[6] Nancy Lewis Tuten and John Zubizarreta eds.,The Robert Frost Encyclopedia,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2001,p.230.
[7]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8] Robert Fagge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bert Fros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1.
[9] 参见杨金才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第3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10] 参见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11] 参见[美]约瑟夫·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刘文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2] Deirdre Fagan,Critical Companion to Robert Frost: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New York:Facts on File,2007,p.378.
[13] Philip L.Gerber ed.,Critical Essays on Robert Frost,Boston,Mass.:G.K.Hall & Co.,1982,p.96.
[14] James Melville Cox ed.,Robert Fros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2,p.58.
[15] John Lynen,The Pastoral Art of Robert Fros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pp.1-2.
[16] [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