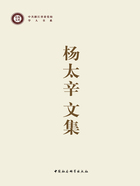
二 壹统类而重实学
荀子对儒家各派的批评,其目的是为明统类,振儒术,以发挥儒家的礼义之统在“齐一天下”过程中应有的指导作用。
儒家“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这说明儒家在宗师作古之后,仍能维持其显学地位。但同时,儒家内部也开始派别纷立,殊趣异路。《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 衰,此辟儒之患”。孟荀同是儒学中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人称孔门龙象。但是,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因此荀子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批评儒家各派以重振儒术的任务。他的儒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是:
衰,此辟儒之患”。孟荀同是儒学中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人称孔门龙象。但是,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因此荀子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批评儒家各派以重振儒术的任务。他的儒学批评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孔子、子弓的评价。任何学派都有自己的宗旨,荀子作为儒者,必然宗师仲尼。但所宗何旨,却因人而异。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太史公自序))后学只能择其所善或所好而从,遂有同宗而异旨的儒家各派。荀子通过对孔子的评价,来确立自己的宗旨,我们可以由此而窥荀学之旨归及其批评之标准。关于子弓,有两说:一说是荀子之师,即传《易》之馯臂子弓;一说是孔子弟子仲弓(即冉雍),当以后者近是。因为,仲弓亲得孔子之传,且孔子对仲弓的评价甚高,列入德行一科。荀子以子弓与孔子并列,可见其侧重于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去取舍宗师之旨,荀子心目中的孔子、子弓是具有以下特征的圣人和大儒:(1)有天下之志。他们以“笞棰暴国,齐一天下”(《儒效》)为己务,“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一国不能独富”(《非十二子》)。(2)法先王之道。他们合天下之英杰,“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顺”;聚“圣王之文章”,起“平世之俗”。这里的“太古”,实际上是指“百王之道”和“千岁之信法”;“文章”,指典章制度,即“礼宪”。《荀子》全书“先王”三十二见,“后王”十二见(据向仍旦《荀子通论》统计),其所重者为“百王之道”和“百王之法”,即治理天下国家的历史经验的结晶,故亦称“先王之道”。(3)明礼义之统。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但荀子却突出孔子“其行有礼”,这是为了其建立礼义之统的需要。(4)通世事之变。这反映了荀子的重视实学的精神,此意荀子屡言之,如“宗原应变,曲得其宜”(《非十二子》),“言必当理,事必当务”(《儒效》)。(5)以仁知为至。“孔子仁知且不蔽”(《解蔽》),因而达于圣王之极,“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解蔽》)。荀子隆礼义不废仁义,并以礼为“原先王、本仁义”之蹊径。《大略》谓礼为仁之表和义之门,“故礼之生,……非为成圣也,然亦所以成圣也”。其学由礼入手,归本于仁义之意甚明。荀子重知,主以认知之心治欲恶之性,不烦赘述。(6)达穷通之理。孔子、子弓与荀子一样,皆是“圣人之不得势者”。因此“心有灵犀一线通”,荀子对他们的“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的抱负节操,慨然言之。荀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而不惜再三申言的孔子、子弓,实际上就是他的理想抱负和人生目标的化身。
(二)对思孟学派的批判。荀子同室操戈,首先把矛头指向思孟学派。他的《非十二子》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儒家八派中,在理论造诣及社会影响上足以和荀子匹敌的,只有思孟学派。子思是否作《中庸》,不能确证。就孟子来说,荀子的批评不能说“查无实据”。试寻绎如下:
(1)“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孟子以“仁义”为先,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礼只是仁义的节文即细则文饰,智只是对仁义的认识理解。他置“仁”于“四德”之首,以“恻隐之心”为“四端”之本,扩其“不忍人之心”,设计“王道”,推行“仁政”,反对功利,尊王贱霸。荀子以“礼义”为统,主张“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不苟》)。他以礼为纲纪,明分使群,正法平政,义利兼顾,王霸并重。因此,他认为孟子法先王“略”而“不知其统”,而在“法先王”这点上,两人并无分歧。
(2)“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孟重《诗》、《书》,荀重《礼》、《乐》。荀子认为只“顺《诗》、《书》”而不能“隆礼”,则虽博而杂,“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劝学》)。
(3)“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孟子盛赞的古代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的经界井田之法,“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的其实什一之赋(《孟子·滕文公上》),皆不见于其他典籍,确有据旧闻造说之嫌。
(4)“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孟荀皆以“知类”、“好辩”自许,这原是百家争鸣的风气使然。但类以统分,说因类异,荀子既断定孟子为“不知其统”,那么势必认定其学术违僻无类,其说解幽隐闭约。然而,从中亦反映出了两者在思维方式、论辩风格及认知途径上的不同。从思维方式看,孟子重主观直觉,善推衍比附。如:“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荀子重客观分析,善类分区别,在此基础上知类察断,以类度类。如他论人,则分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论儒,则评俗儒、雅儒、大儒;论君,则品明主、暗主、昏主;论国,则辨王、霸、安存、危殆、灭亡等等,真可谓知通统类。从论辩风格看,孟以气胜,辞锋犀利,踔厉风发,善设机巧,引人入彀;荀以理长,条分缕析,朴质平实,博大深厚,足以服人。从认知途径看,孟荀都重视心的作用,但孟子内向,迷信天赋良知,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只要尽心知性,就能知天,完成认识一切的任务。因此,荀子说他“闭约”。荀子外展,重视假物致知,提倡稽物壹道,真积力久,由“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达到“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解蔽》)之境地。
(三)对其他各派的批评。荀子笃实,他不但重视礼义,而且重视礼法、礼信、礼文。他对思孟学派的批评,侧重在义理方面,而对儒学其他各派的批评,则侧重在言行方面:“弟佗其冠,衶 (冲淡)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非十二子》)
(冲淡)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非十二子》)
这里所说的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不必是实指其人,而是指其后学。须知任何学派开创之初,未始没有精意胜义,而往往坏于徒具虚文而不知其义的末学附从。荀子对贱儒或俗儒的批评,其旨还在“壹统类”而重笃行。通过批评,他从礼法,礼信、礼文甚至礼容等方面,坚持了礼义之统。其中特别对某些儒者的“术缪学杂”、百无一用和“衣冠行伪”,志意卑下,尤为深恶痛绝。有的学者认为荀子骂人每每不揭示出别人宗旨,而只是在枝节上作人身攻击,恐非其实。《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说:“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荀子的学术批评,词义过当之处,容或有之,然正如王先谦所说:“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有齐一天下经世致治之志,而儒者或迂远,或虚伪,或卑下,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其言辞不免偏激,但其主旨不可谓不正也。
荀子的儒学批评,对儒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与孟子及三氏异趣,但相反亦相成也。孟子之重仁义礼知,荀子之重礼义仁知,只是着手处不同。此外,如子张之宽容,子夏之笃学,子游之礼治,都在荀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正是这种激浊扬清的批评精神,赋予儒学以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