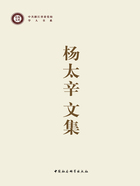
三 齐言行而贯大道
荀子通过评估群经“隆礼义”,批评儒家各派“壹统类”,而对诸子百家的批判则是为了“齐言行”。“齐言行”是“齐一天下”的前提,其内容包括对“诸侯异政”的政治批判和对“百家异说”的学术批评,现仅就其学术批评而言。荀子的学术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总方略”和“一制度”,以达到由霸而王的政治目标,其批评锋芒触及墨、道、名、法及纵横等家。但是,荀子又是当时最博通的学者,重文化、重理智,对诸子的合理内核和真理因素,又广为吸收融合。因此荀子的学术批评,既有政治标准,又有学术标准,而两者又统一于治国之道。从《非十二子》,《天论》、《解蔽》等篇,可以看出荀子的诸子批评的主要内容和批评思想的演进轨迹。
(一)辨治乱,辟“邪”去“奸”。
《非十二子》集中体现了荀子学术批评的政治标准。文章开宗明义就指出:十二子“饰邪说,文奸言,以枭(挠)乱天下、矞宇嵬琐(谲诡委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他侧重于以“治乱”论是非,以是否合乎礼治作为批评的标准。如:“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它嚣,不详,或说是环渊。魏牟,魏国公子,又称中山公子牟,约与庄子同时。《汉书·艺文志》有《公子牟》四篇,《庄子》之《秋水》和《让王》,《战国策·赵策》皆记载其言行,似属于道家的纵情玩世、放浪形骸的一派。荀子对他们的批评,着眼于不足以“合文通治”这一点。“礼之敬文也”(《劝学》),他们的行为不合“文”则悖礼,悖礼则不足以治世。荀子又认为人性恶,只有节以礼义,才能由恶趋善。“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性恶》)。“纵情性、安恣睢”则“偏险悖乱”,必不能通向“正理平治”。
荀子认为“齐一天下”在于“维齐非齐”,治国在于“明分使群”。礼对天下国家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辨异”和“明分”:“礼别异”(《礼论》),“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相》),“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而墨子崇尚亲立事功,使天子百官“皆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过分主张俭约,使天子百官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上下泯没差等,官民无法辨异,君臣没有悬隔。这样势必使天下乱贫,社会解体(《富国》)。这充分反映了荀子以礼治国论的封建特征。但其中也反映了社会必须分工、分职的合理思想。宋钘“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庄子·天下》),其主张与墨子有相似之处,或以为墨子支派,故荀子将他与墨子并列,一起非之。
慎到、田骈皆黄老学者,兼治道法。慎到说:“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乱”,故荀子说其“终日言成文典”;他认为:“以道变法者,君长也。”故荀子说其“取听其上”;他还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佚文》)故荀子说其“取从于俗”。要之,荀子认为“礼义生制度”、“礼者法之大分”,反对离开礼义“擅作典制”。因此,他无视慎到思想的合理一面,断定其不足以“经国定分”。
对惠施、邓析,荀子不是非议其好辩,他声称“君子必辩”,而是非难其辩“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他认为“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正名》)故认为惠、邓之辩不足以“治纲纪”。
综上所述,荀子在这里以礼为标准,从纲纪名分和经国致治等方面来是非诸子,因而词峻义严,不稍宽假,虽不否认其“持之有故”和“言之有理”,但因其“足以欺惑愚众”,均予非之。
(二)察是非,纠偏解蔽。
荀子的《天论》和《解蔽》则从“知”的角度论百家,以“道”为准评是非。虽然他认为诸子皆有“偏”和“蔽”,不可谓“知道”,但并不否认他们皆得道之一端或一隅。
《天论》的主题,是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以人道“应”天道和“制”天命。文章的最后两段,在对百王之道的“大体”与诸子之道的“一偏”进行对比之后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奇);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对四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既不否定他们的“有见”,又指出了他们的“无见”。但是,有见于偏,不见其全,不可谓知道。因为,荀子的道是“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即君国治人之道。因此,“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这里,他以是非论治乱,目的在于纠偏以知道。
《解蔽》是荀子学术思想的高峰之作,也是他学术批评的纯熟之作。文章已经脱略了《非十二子》式的剑拔弩张、咄咄逼人的声气,从容论道,剖析入微。一开始就指出:(1)百家未尝没有“一曲”之见,只是不得“大理”之全。(2)肯定其用心“莫不求正’,而只是由于主观上“妒缪于道”,客观上他人“诱其所迨”,因而失其所求。(3)指出其认识上的根源是“私其所积”和“倚其所私”,即蔽于自己的一得之见,而不能知人之长。接着他言简意赅地评析了诸子在“道”上的得失: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
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
荀子认为上述诸子之道,不失为道之“一隅”;其失在于一个“尽”宇,他们蔽于所见,而以一隅之得为道之全量。“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君子应知“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劝学》)。因此,欲求全尽粹美之道,必须解除心术之患,虚壹而静,用心知求道。所谓虚壹而静,就是不以已知拒未知。不以彼一害此一,不以杂念乱心知,这就是“解蔽”之道。
(三)合王制,融贯各家。
荀子在《解蔽》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与不合王制也”。以“王制”为标准,在非中察是,在是中察非,这是荀子学术批评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所谓“合王制”,说明荀子的一切理论学术活动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替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设计方略和制度。在非中察是,因而他能成为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在是中察非,因而能将儒学推向新的阶段。
根据上述的批评原则,他吸收了墨子的尚功用的思想,而制之以礼义:吸收了宋钘的“虚壹而静”的心术,而去“情欲寡浅”,吸收了申不害的重术势的思想,而去其“权谋势诈”,形成了自己的“道术”观:吸收了慎到的重法思想,去其“绝圣弃知”,形成自己的“道德”观或“礼法”说;效法惠施的好辞善辩,去其舛驳无统;借鉴庄子的天道自然的思想,而去其逍遥无为。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他深宏博大的思想体系。
综上所述,荀子的诸子批评所用的标准,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可执一而论。大体说来:一是从“治”的角度看,以“礼”为标准,由“治乱”论“是非”,这可谓政治标准;二是从“知”的角度看,以“道”为标准,由“是非”论“治乱”,这可谓学术标准;三是从“齐一天下”的角度看,以“王制”为标准,不但兼察是非治乱,而且非中察是,是中察非,这可谓理想的标准,即政治和学术统一的标准。当然,荀子的批评思想有一个在批判实践中完善的过程,由《非十二子》经《天论》到《解蔽》,大致反映了这个演进的轨迹。总之,荀子学有宗旨,不守门户,严于去伪,慎于纠偏,兼收并蓄,归本实践,这种批评思想是可取的。
荀子的学术批评,不但为我们留存了先秦儒学和诸子的精神风貌,保存了大量学术文化资料,而且他的批评原则和方法,金声而玉振,后学承继不绝。简而言之,从《淮南子·要略》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可略睹荀子之影响。